

配图来自网络

![]()
那段藏在时光里的“偷狗”犬缘
○ 初山
其实我骨子里挺霸道的,那年我8岁,铁定认为村东南角二蛋家的那条小黑狗,就是我的。
第一次见小狗,是在他家西边的大土堆上。那天我和几个伙伴玩捉迷藏,正猫着腰躲在酸枣树后,一抬头就撞见了那双眼睛。小狗刚满月,浑身的毛纯黑得像染了墨,唯有胸口缀着一撮雪白的绒毛,像落了片雪花。它圆滚滚的身子撑在四条小短腿上,黑亮的眼睛湿漉漉的,不错眼珠地望着我,没有生分,没有警惕,倒像久别重逢的亲人,眼神里裹着温热的亲近,一下子勾走了我的爱怜。我试探着伸手,它竟顺着土坡滚下来,毛茸茸的身子蹭着我的手心,尾巴摇得像团小绒球。
从那天起,每个放学的黄昏,我都要绕路去看它。田埂上的野草窜到膝盖高,我踩着晒得温热的泥土,听着蝉鸣一路欢唱,远远就能看见它蹲在二蛋家大院的门槛边,像个小小的哨兵。见了我,它就迈着小短腿跑过来,围着我转圈圈,有时还叼着我的裤脚往院子里拽。
我那时刚上小学一年级,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,自认力气和心智都足够把这小狗带回家。那份念想像地里的野草疯狂滋长,让我寝食难安,饭桌上扒拉几口就放下,夜里躺在床上,眼前全是它摇尾巴的模样。
母亲生我前已有三个姐姐,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,自小被父母捧在手心。父亲从地里回来,再累也会把我举过头顶;母亲总是把好吃的给我留着,知道我嘴馋。算卦先生说我眼睛清亮透着灵性,将来定有大出息,这话让父母对我寄予厚望,我的心愿,他们总能悄悄记在心里。
小孩的心事藏不住,木讷老实的父亲很快就看穿了我的秘密。父亲皮肤黝黑,手上布满老茧,少与人交往,家里大事小情多由母亲打理——母亲善良热忱,村里红白事、谁家有难处,她都主动搭把手,威望颇高。可二蛋家不同,他们是村里的殷实人家,高门大院,朱红大门漆得鲜亮,院墙比别家高出一截,院里是青砖瓦房,和村里大多土坯房格格不入。二蛋的父亲开着县里少有的大卡车,走南闯北;爷爷年轻时练过武术,腰板挺直,眼神锐利,村里没人敢轻易招惹。我们两家素无来往,像是活在两个世界。
那年夏天快放暑假时,空气湿热得像裹了层棉絮,蝉鸣聒噪得让人心里发慌。我揣着母亲烙的白面饼,壮着胆子走进了二蛋家敞开的大院。天热,院里静悄悄的,石榴树的影子拉得老长,大狗不在,二蛋也没踪影,只有小黑狗摇着尾巴朝我跑来,鼻子嗅着我口袋里的香气,眼神急切又乖巧。
我蹲下身把饼掰成小块喂它,它吃得狼吞虎咽。看着它可爱的模样,我心底的念头愈发强烈。我站起身往院门外走,一边走一边回头唤它,它竟寸步不离地跟着,小短腿哒哒地跑着,穿过田埂,穿过开满野花的小径,穿过槐树林,一路跟着我进了我家院子。
我家院子挺大,收拾得干净利落,墙角搭着兔窝,房后栽着五棵大槐树,枝繁叶茂遮出大片阴凉。父亲刚从地里回来,肩上扛着锄头,裤脚沾满泥土,见了小狗眉头微微蹙起:“这是谁家的?”
“二蛋爷爷家的,它跟我亲着呢!别人路过它都咬,就对我好,总跟着我。” 我仰头望着父亲,眼神里满是恳求。
父亲看着我,又看了看围着我裤脚打转的小狗,眼神渐渐温和:“人家的孩子也疼狗,咱们家兔子刚下了崽,送两只过去,不欠人情。”
我急了,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,对着小狗嘟嘟囔囔:“你是我的狗,我要养着你,我会对你好的,给你吃最好的东西,带你去河里玩……”说着说着,眼泪就掉在了地上。
小黑狗在我家安了家,三姐给它取名“阿采”。三姐那时已是中专毕业的老师,戴着眼镜,带着书卷气。她捧着一本封面发黑的旧书,坐在槐树下的石凳上,摸着小狗的头说:“这狗的‘狗性’好,通人性,与咱们家有缘,你得好好待它。” 我追问名字的由来,她只笑不说。
后来我才知道,那本书是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。多年后我在大学图书馆偶然翻到这本书,看到“孩童在天真和善忘中,开始创造游戏,诉说神圣的肯定,让精神有自己的意志”这句话时,忽然懂了“阿采”这个名字里藏着的深意—— 那是三姐对生命灵性的期许,也是对我童年纯粹的守护。
那年代家里清苦,日子过得紧巴巴,白面饼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,平日里多是玉米饼子就着咸菜。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,总会偷偷留给阿采。母亲给我煮的鸡蛋,我剥了壳喂它;父亲买的糖块,我咬成小块塞进它嘴里。总之,我最爱吃的东西,也舍得掰一半放在它的碗里。阿采从不挑食,给什么都吃得香甜,它的毛越来越油亮,眼睛越来越有神,总在我面前摇尾撒欢,有时还会叼着我的鞋带,把我往门外拽,邀我一起去玩。
谁知阿采来家第三天就病了。那天清晨,我去叫它,见它蜷缩在兔窝旁,浑身发抖,眼神黯淡,没过多久就开始上吐下泻,蔫蔫的没一点精神。村里的小笨狗向来皮实,极少生病,母亲急得团团转,四处托人打听药方。父亲看着我熬红的眼睛,没多说什么,默默找来一块旧棉絮铺在我的床底下,把阿采抱了过去。
夜里,月光透过窗户洒在阿采虚弱的身上,蛙鸣阵阵,虫声唧唧。我躺在床上听着它微弱的喘息声,翻来覆去睡不着,悄悄爬起来蹲在床底下轻轻抚摸它的背,它的身子滚烫,喉咙里发出细细的呜咽,像是在诉说难受。
后半夜,我听见父亲轻轻起身,拿起墙角的蓑衣披在身上,小心翼翼地抱起阿采推开房门走了出去。我悄悄跟在后面,看见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,蓑衣被月光照得泛着银光。父亲是去了村头相爷爷家——相爷爷是村里有名的老中医,谁家有人生病都愿意找他。
我趴在窗外,听见相爷爷摸着阿采的肚子笑着说:“没大碍,是撑着了。这小狗通人性,怕是你们家孩子太疼它,把好吃的都给它吃了,肠胃受不了。”父亲憨厚地笑了笑:“孩子把它当个宝。”相爷爷开了些消食的草药,嘱咐用温水煎了给阿采喝,不要再喂太多东西,只让它喝些温水。
接下来的三天三夜,我几乎没合眼,一直守在阿采身边。父亲按照相爷爷的嘱咐,每天给阿采煎药,用小勺子一点点喂它;母亲煮了软烂的小米粥,让我偶尔给阿采舔几口。我把阿采贴在怀里,感受着它渐渐降温的体温,心里默默祈祷。终于,阿采痊愈了,那天清晨它挣脱我的怀抱,摇着尾巴跑到院子里对着天空叫了几声,声音清亮,又变回了那个欢蹦乱跳的小家伙。
往后的日子,阿采成了我的影子,形影不离。房后的五棵大槐树是我们最常去的地方,夏天树枝繁叶茂,遮出大片阴凉,我坐在房顶读《情满青山》《保卫延安》《苦菜花》《红楼梦》《茶花女》这些中外名著,阿采就趴在我身边,有时会把我放在地上的书叼到房顶上,用脑袋蹭我的手,像是在催我快点读。
我也常带着阿采去房后的河里玩。那条河蜿蜒东行,又向南流,过了桥往东南方向而去,正好包围着我们家,村里人都说我们家风水最好。河水清凌凌的,游鱼可见,河岸边长满芦苇和野草,春天有甜甜的笋尖,夏天有清脆的蛙鸣,秋天有饱满的野果。我和阿采在河里抓泥鳅、捞鱼,用筛子抄起一尾尾小鱼,看着它叼着小鱼在岸边奔跑;我们在河边垒土埝,筑成小小的堤坝,看着河水漫过堤坝溅起细小的水花;我们躺在河边的草地上,听小鸟鸣叫,看天上白云飘过,日子过得惬意又自在。
母亲总说我从小就馋,嘴角那颗痣是“口福痣”。小时候偷摘人家梨子、爬瓜地偷瓜的事,我也干过不少,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村里放电影那天。我们几个孩子觉得电影没意思,相安提议去偷五女家的大梨,我和另一个伙伴立刻响应。
五女家的梨树长在院子南边,树枝伸出院墙越过房顶。我们悄悄爬上房顶,瓦片冰凉,踩在上面发出轻微的“咔嚓”声。梨树上挂满了大大的梨,月光下泛着黄澄澄的光泽,我们迫不及待地摘了大口吃起来,又脆又甜的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。
正当我们准备再摘几个装裤兜里带回家时,院子里传来脚步声。五女没去看电影!她听见房顶上的异响,拿着手电筒走了出来:“谁?”我们吓得魂飞魄散,赶紧沿着房顶北侧的树往下爬。相安和另一个伙伴年龄大些,身手敏捷,一下子就滑下去跑没了踪影。我年龄最小,身子瘦弱,爬得慢,眼看就要被抓住。
就在这时,一直守在树下的阿采忽然冲着五女疯狂叫喊起来,毛发竖起,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,一步步朝着她逼近。五女被吓得连连后退,手里的手电筒都掉在了地上。我趁着夜色朦胧,赶紧从树上滑下来,拉着阿采就往远处跑,直到跑回家里,心还在怦怦直跳。
多年后我和五女偶然重逢,说起这件事,她哈哈大笑:“我那时候早就认出你来了,你不过是个从犯,那几个坏小子比你坏多了。我管你妈叫婶子,听婶子说过你特别馋,就放了你一马。”后来这位大姐经常去城里卖水果,城管没收过她的车子和秤,我得知后还帮她协调了一番,也算偿还了当年的“偷梨之债”。只是从那以后,无论村里村外种的桃子多么又大又红,在我眼里,永远没有小时候偷来的梨子香甜——或许是因为那份偷偷摸摸的快乐,或许是因为阿采护着我的那份勇敢,让那段记忆变得格外珍贵。
变故发生在我上初中时。那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,忽然传来消息,二蛋的父亲开车出门时与人斗殴,被打成重伤,送进医院后没多久就去世了,案件始终没有侦破。二蛋的母亲哭得撕心裂肺,没过多久就收拾行李远走他乡,再也没有回来。二蛋的奶奶受不了这打击,日夜以泪洗面,身体一天天垮下去,没过几个月也撒手人寰。往日热闹的高门大院,一下子变得冷清破败,只剩下二蛋和爷爷相依为命,家道中落。
从那以后,父亲总往二蛋家跑。有时带着家里刚蒸好的馒头,有时拎着地里摘的青菜,有时帮着干农活、收拾院子,更多时候,只是陪着二蛋的爷爷喝酒。
一个雷雨交加的中午,天阴得像墨染的一样,闪电划破夜空,雷声轰隆隆地响,震得窗户都在发抖。已经十二点多了,父亲还没回家,母亲有些着急:“去喊你爸回来吧,是不是又去二蛋家了。”
我披上雨衣,小跑着往二蛋家赶。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,模糊了视线,田埂泥泞湿滑,我好几次差点摔倒。二蛋家的院子里一片荒芜,石榴树的叶子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,朱红色的大门掉了漆,显得格外破败。我走到窗前,透过纸窗上的一个小洞往里看,屋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,灯光摇曳,映出两个沉默的身影。
二蛋的爷爷坐在土炕上,面前的小桌上摆着一壶酒、两个酒杯和几个小菜。他大口大口地喝着酒,酒液顺着嘴角往下流,浸湿了衣襟。父亲坐在对面,平日里木讷的他,竟也端着一杯酒一口饮尽,眼角泛红。雨越下越大,雷声越来越响,他们没有发现我,只是默默地喝着酒。
忽然,二蛋的爷爷嚎啕大哭起来,声音嘶哑:“我的儿啊,你怎么就这么走了……”他一边哭一边捶打着自己的大腿,肩膀剧烈地颤抖。父亲没有说话,只是从炕桌这头挪到那头,挨着老人坐下,伸出粗糙的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。他拿起酒壶,给老人和自己都满上酒,然后端起酒杯又一口饮尽,眼里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,砸在酒杯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
爷爷的哭声渐渐变成了抽泣,父亲依然没有说话,只是不停地给老人夹菜、倒酒。两个男人在雷声和雨声中喝着无言的酒,那份沉重的悲伤,透过纸窗的破洞深深感染了我。我悄悄地退了出去,冒雨赶回了家,对母亲说:“爸爸不在二蛋家,是不是赶集去了?”母亲疑惑地说:“下这么大雨,谁还会赶集?”
后来母亲还是知道了真相,只要父亲不在家,一定是去了二蛋家。受父亲的影响,我也经常去二蛋家帮他补习功课。二蛋的学习成绩不好,爷爷天天督促也没什么效果,我便每天放学后去他家,陪着他写作业、讲解难题。慢慢地,二蛋的成绩有了很大进步,爷爷特别高兴,经常当着别人的面夸我:“这孩子懂事,有出息。”
我没有见过我的亲爷爷,父亲说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,享年五十岁。有一次,我揣着大舅给买的、带着神奇酒香味的面包——在当时算是稀罕物——偷偷跑到二蛋家。二蛋的爷爷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,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。我走到他身边,把面包递给他:“爷爷,这是我大舅买的,可好吃了,你尝尝。”他抬起头,看见面包,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光。我鼓起勇气说:“爷爷,我没见过我的亲爷爷,你就当我的爷爷吧。”
老人一把将我搂进怀里,力道大得几乎让我喘不过气,哽咽着说:“好,好啊,好孩子。”他的怀抱很温暖,带着淡淡的烟草味和岁月的气息,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我又有了爷爷。
我总固执地觉得,二蛋家的变故,与我“偷”走阿采有关,心底藏着说不清的愧疚。这份愧疚,让我更常去帮二蛋补习功课,看着他的成绩渐渐变好,爷爷脸上露出笑容,我才稍稍心安。我也总给二蛋的爷爷带些好吃的,陪他说话,听他讲年轻时练武术的故事,讲二蛋父亲小时候的趣事。
高考那年,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三姐说我是整个家族的希望,父母虽然没说什么,但我能看出他们眼中的期盼。可命运弄人,我高考失利了,离分数线差了三分。我很懊恼,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不愿意见人。
那天雨下得很大,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淹没。我一个人跑到废弃的刘家大门“祖屋群”里发呆。老屋早已破败不堪,墙角长满青苔,蛛网遍布,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潮湿的气息。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,看着窗外的雨水冲刷着墙壁,心里充满了绝望。
三姐到处找我,父母也急得团团转,村里的人都帮着打听我的下落。雨越下越大,忽然间,我听见门外传来熟悉的叫声,是阿采!它不知从哪里跑过来,浑身湿透,毛发黏在身上,显得格外狼狈。它跑到我身边,使劲地叼着我的裤脚往门外拽,眼神急切,像是在催促我快点离开。
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这么着急,可看着它焦急的样子,我还是站起身跟着它往外走。就在我们冲进雨中的一刹那,身后传来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老屋的一角轰然塌陷,砖头瓦块砸下来,扬起一片尘埃。我回头望去,吓得浑身发抖,如果不是阿采,我恐怕已经被埋在废墟之下了。我看着雨中步履蹒跚的阿采,它的毛发被雨水淋湿,紧紧贴在身上,显得有些苍老,可眼神依然坚定,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阿采的眼神里,藏着某种预知的灵性,它是来救我的。
复考揭榜那天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骑着自行车去县城看榜。一路上心怦怦直跳,既期待又害怕。到了县城的大操场,红榜已经贴在墙上,文理科混排,密密麻麻的名字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我深吸一口气,顺着名字往下找,忽然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看见了我的名字!那一刻,狂喜淹没了所有的忐忑和不安,我几乎要跳起来,真切体验到了金榜题名的喜悦。
我没有立刻回家报喜,反倒骑着自行车去了姥姥家村南的漕河。那是1982 年,河水清凌凌的,游鱼可见,芦苇荡漾,鸟声啁啾,景色宜人。我在河边坐了一整天,看着河水静静流淌,听着鸟叫虫鸣,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儿时——老舅在高高的大堤上彻夜吹着长箫,箫声悠远,回荡在夜空里;我躺在他的怀里,听着虫鸣鸟叫、蛙鼓玄冥。阿采蹲在一旁,静静地陪着我。那箫的旋律一直回荡在我的梦境里,直到现在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,历历在目。
回到家时天已擦黑,月亮洒下清辉。父母还没吃饭,煮好的面条早已坨了,放在桌上,旁边还摆着一盘韭菜炒鸡蛋,是我最爱吃的。我哭丧着脸不说话,过了好一会儿才说:“妈,我想吃煎腊肉。”
母亲起身,默无声响地走进厨房,和面、切腊肉,动作麻利。父亲坐在一旁,默默地看着我,一颗又一颗地抽着烟。看着腊肉煎得焦黄,香气四溢,我才笑着说:“妈,我考上了!”母亲又哭又笑,一边擦眼泪一边说:“你个臭小子,考上了还不早点说,让我和你爸担心。”她絮絮叨叨地说:“你复习的那年,穿着一条带补丁的裤子,现在要去新学校上学,妈心里不好受啊,可是家里没钱,没法给你做新裤子。”
那天夜里,全家人围坐在桌前,吃着饭,说着话,笑声不断。姐姐和弟弟妹妹也都围绕着我,幸福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大院。可我却忽略了阿采,没能和它分享这份喜悦。

配图来自网络
直到第三天,父亲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,阿采丢了。我才知道,发榜那天,父亲带着阿采去地里干活,他累了,在田埂上睡着了,醒来后就不见了阿采。父亲找了两天一夜,跑遍了附近的村里村外,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只黑色的狗,胸口有一撮白毛。他瘦了好几斤,眼里满是红血丝,声音沙哑。
母亲偷偷告诉我,父亲怕我伤心,一直瞒着我,可他吃饭时总下意识地往桌下看,像往常喂阿采那样,筷子夹着菜就想往下递,发现桌下空无时,眼神里满是失落。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难过,他一向坚强,可那几天我分明看见他偷偷抹眼泪。母亲说,父亲的胃病,就是从那时落下的,往后吃饭总心不在焉,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
阿采平时也会跑出家去,但天黑之前总会回来,它一向忠诚顾家,村里人人都知道我们家的阿采厉害,任何贼和惦记我们家宝贝的人,都无法进入院子。我总觉得阿采的失踪是天意——它已经十几岁了,相当于人的七八十岁,或许是寿终正寝,或许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离开了。若真要让我经历与它的生死别离,那份悲痛,恐怕我难以承受。
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县委机关工作。那年腊月三十,父亲走了十几里地来县城看我,他穿着一件旧棉袄,头上戴着棉帽,脸上冻得通红,手里还提着一个布包,里面装着家里种的花生和红枣。他是想让我带着妻女回家过年。
可妻子嫌家里条件差、天太冷,孩子还太小,不愿回去。我劝了她很久,她还是不同意。我只能骗父亲说:“她单位太忙,过年有案子要办,回不去了。”父亲听了,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,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。
我把父亲安顿在招待所,然后去妻子单位找她,回来后还是那套说辞。父亲沉默了很久,说:“那你们好好过年,不用惦记我和你妈。”第二天一早,我去招待所送他,却发现他已经走了,床上叠放着整齐的被褥,桌子上放着他带来的花生和红枣,一个都没动。
我走出县委大院,看见父亲佝偻的背影,他正一步步朝着城外走去,走得很慢,背影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孤单。我忽然看见他抬手抹了抹眼睛,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寒风中掉眼泪。从那以后,几乎每一年过年都是我一个人回家,父母再也没有提过让我带妻女回家的事,他们把那份说不出来的情感,压抑在心中。
父亲在我考上大学后又活了十九年。这十九年里,我忙于工作和家庭,回家看望他们也不是很多。印象最深的是给父亲买过两条 “小熊猫” 牌香烟——当年最好的烟。父亲一直抽着旱烟,说纸烟没劲儿,他把那两条烟放了很久,舍不得抽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不是不喜欢,而是不愿让我花钱。
父亲这辈子,从来没有开口朝我要过钱,也没有提过什么要求。直到他去世前一天下午,我和朋友回家看望他,他忽然说想吃石榴。我的记忆当中,这是他一辈子唯一朝我要求过的事情。
我把朋友安顿在乡下的家,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到城里。那是阴历的九月十八,天已经有些凉了,我走了一大圈,也没碰见卖石榴的,心里很是颓丧。就在我准备往回走的时候,来到七一路新市场北侧交叉口,忽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,车后座上放着一个大筐。我大喜过望,大叫一声:“有石榴吗?”
他猛地刹车,回头说:“有。”我一下子把他的石榴都包了圆儿,记得有七八个,红彤彤的,看着就喜人。我骑车飞快地回家,父亲看见石榴,眼睛亮了起来,他一口气吃了一个大石榴,嘴角沾着石榴籽,像个孩子一样,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我看着他的样子,心里暖暖的,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孝顺他,可谁也没想到,父亲在第二天凌晨三点多就去世了。
母亲怕半夜惊扰我,一直到天亮才让弟弟告诉我。我赶回家时,父亲已经冰冷了,他静静地躺在床上,脸上带着一丝安详。母亲说,你爸一辈子就说过一回贴心话,就是前一天下午,我在院子里拍豆子,他说:“累了就歇会吧,累病了谁管你呢!”
父亲出殡那天,家里来了很多人,我好多朋友都去了,村里的人都来送他最后一程。我一直强忍着泪水,因为我是长子,家里还有很多事要办,我不能倒下。就在父亲被抬起来,放在那个小床上,推向焚尸炉的时候,我看着他有些凹陷的嘴和牙齿,看着他灰白色的脸,那张沟壑纵横的、承载了太多艰辛的脸,一刹那间我崩溃了,泪水像决堤一样,再也控制不住。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面,我们父子从此永别了。
父亲去世后,母亲才告诉我当年阿采的真相:阿采根本不是我“偷”来的。父亲看出我对阿采的执念后,竟放下了他木讷的性子,一次次跑到二蛋家,陪着二蛋的爷爷喝酒、说话,慢慢拉近了关系。他跟二蛋的爷爷说,孩子太喜欢那只小狗了,能不能让孩子“偷”走,就当是成全孩子的心愿。
二蛋的爷爷起初舍不得,二蛋也非常喜欢那只小狗。可父亲一次次上门,态度诚恳,二蛋的爷爷最终被打动了。父亲精心策划了那场“偷狗”:他让人把大狗牵走,又让二蛋的姑姑把二蛋接走,家里就只剩下那条刚满月的小狗在院子里跑,等着我上门。母亲说:“你爸这辈子不爱求人,性子又倔,可为了你,他什么都愿意做。”
原来,那场看似偶然的“偷狗”,是父亲用沉默的爱,为我编织的一场温柔的约定。他用自己的方式,圆了我儿时的心愿,也悄悄维系了两家人的情谊。
如今想来,阿采的到来,是一场缘分的指引,更是父爱的见证。它让内向孤傲的我,学会了释放温柔,懂得了人与万物的羁绊。而父亲的爱,就像房后的大槐树,沉默矗立,却为我遮风挡雨,留下满院清凉。
岁月流转,槐影依旧,阿采的吠声仿佛还在耳畔回响。那场被策划的“偷狗”,那段藏在时光里的犬缘,还有那份沉默如山的父爱,早已刻进我的骨血,成为生命中最温暖、最珍贵的印记。每当想起阿采,想起父亲,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温馨与感动,它们像一束光,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,让我明白,唯有爱,才是永恒的归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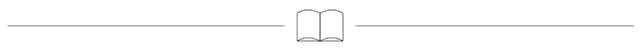

(刘君福,笔名:初山,中国剧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,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,保定市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,保定影视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副主席,保定市作协莲池区作家协会副主席,保定市诗词协会莲池区、竞秀区副主席,保定微短剧协会监事。出版文集《嚎啕的鸟》,作品多次获奖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