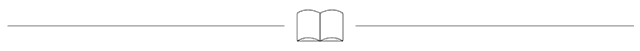![]()
那山村,那山民
○ 李斌
一
我当年插队落户的山村,近百户人家,和别的村子比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,然而,她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。
“隐将”这个村名,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有点神秘。这不仅是因为她所处的位置很隐蔽:从远处看过来,她坐落在两条山沟交汇的底部,四周被高山包围着,一条落差分明的溪流S形横着穿过村头。村头很窄,两边各有一块陡峭的大岩石耸立着,像两把石剑铸成一个大闸门,清澈的溪流从“闸门”中潺潺流过,溪流旁有一棵千年古樟,俨然一位雷打不动的卫士,倚着两柄宝剑,守卫着村庄的安宁。
隐将村的神秘,更是因为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扯上了关系。她坐落在小有名气的大明山南麓,大明山位于临安和淳安交界处,海拔1100多米。临安这一侧,多悬崖峭壁,峰石嶙峋,瀑布飞泄,有“小黄山”之称。而淳安这一侧,平坦开阔,有300多亩草甸,当地人称“千亩田”。相传朱元璋曾在此屯兵、开垦。村里的老人说,朱元璋在“千亩田”时,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,梦中有一位高人告诉他,南边山脚有个小村落,隐居着一位异人,可以请来帮助他打天下。朱元璋第二天就带着人下山,按照梦里所述情景终于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了这位异人,却发现此人虽然长得高大,但从小就一直躺在床上不会走路。朱元璋悲从中来,便倒了一碗水给此人喝,眼泪禁不住滴落进双手捧着的碗里。不料此人喝了渗有“天子泪”的水后不仅立即就站起来了,而且力大无比。日后果然成为朱元璋麾下的一员骁将。
隐将村当时叫隐将大队。隐将大队由三个自然村组成,从空中俯看下来,三个自然村呈三角形,外面的两个角分别是石井村和外坪村。但平视过去,这三个村不在同一海拔上,外坪村最低,有一条乡里过来的机耕路,逆着弯曲蜿蜒的溪水,可抵达隐将村。而石井村在北面的山腰之间,各有一条山间石阶小路下到隐将和外坪。从风水上看,隐将村坐北朝南,石井村和外坪村有点应了“左青龙,右白虎”的玄味;如果从军事上看,由石井村和外坪村一左一右扼守着前方,形成犄角之势,隐将村则是个可守可退的安营扎寨绝妙处。
隐将人去一趟公社(乡)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机耕路。虽然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,但隐将人热情好客,淳朴敦厚。无论家境好孬,凡遇有路人经过家门口,这家主人必定会含笑招呼路人:“到屋里来吃清茶!”隐将人的茶,都是自制的炒青毛茶掺进薄荷,盛入以老透了的葫芦制成的器具里,葫芦干皮隔热性好,使茶水冬暖夏凉,尤其是夏天,这盛在葫芦里的薄荷茶,喝起来让人清凉提神,是名副其实的“清茶”。
隐将人世世代代为汉族,但在穿戴等风俗方面都类似畲族人。女人们常年佩戴刺绣花围裙和头巾;男人们的服饰风格古朴,衣服有对襟,袖宽。外出干活喜欢腰系素色围裙,腿缠绑带。
二
我刚到隐将村时,住在房东家。房东夫妇三十来岁,生了四个女儿。因为超生被罚过款。由于小孩多,房东在他们章姓大家族的同辈兄弟姐妹中,家境偏下。在夜间,我时常看见房东大哥点起煤油灯,端坐在堂间织麻布。这种老式织布机由挡板、踏板、麻绳、机杼等木(竹)质构件组成,竹子制成的梭子牵着麻纱,在房东大哥两手间左右穿梭,撞击织机的“哐当”声和踏板的“吱呀”声,将经纬线编织成优美而流动的韵律。房东大嫂则坐在一旁的绣架前,身旁放着装有剪刀、顶针等工具的绣篮,就着暗淡的光亮,在彩色棉线绕以土布做底的线板上穿针引线,针尖不时地在她的发髻上滑过,将劳作的艰辛刻画成一幅恬静而优雅的画图。他们的大女儿红花才十岁出头,有时也在大门口支起绣架,像模像样地飞针走线。
不仅我的房东家,隐将的小姑娘都喜欢坐在门口绣花。隐将人把尚未出嫁的女孩叫做“囡婴种”,已婚女人叫做“囡婴家”。“囡婴种”一般都穿母亲或自己做的绣花布鞋,而“囡婴家”则穿不绣花的素布鞋。“囡婴种”如果到了出嫁的年龄还不会绣花,那是嫁不出去的。
我第一次走进房东夫妇住的房间时,见房间一角的火盆里仍然生着炭火。当时正值夏天,我颇感意外。房东大哥对我说:“我们山里人家都这样,家里的火盆常年不熄,冬天取暖,其它日子用来烧开水。”我这才看清,火盆的正上方果然吊着一把由铁链条挂着的已被熏得漆黑的铜茶壶。后来我发现,大山里夏天的晚上并不太热,用厚厚的炉灰覆盖着火盆里的炭火,火盆对房间温度的影响确实不大。
房东的房子地势较高,站在门口的晒谷平台上,可以俯瞰半个村子。后面是一个小坡顶,这个小坡顶是村里三个小队的队长通知社员出工的最佳位置。那时的农村,“通讯基本靠吼”。他们用来“吼”的,是我们读小学时作土广播时用过的那种铁皮喇叭。每天,天蒙蒙亮,睡梦中的我便被屋后山坡上的三个小队长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派工声喊醒。他们拖腔拖调如同唱戏一般,讲的都是当天出工的内容、地点以及注意项等,尽管重要的事情他们都重复说了三遍,但在较长的时间里,我无法听懂他们在说什么,需要房东给我翻译。
两个月后,我离开了房东家。和三小队的另一位知青小罗挨在一起住,各自一小屋。小队里还分别分给我们一块菜地,也挨在一起。我们的菜地虽然地势平坦,且离溪水较近,但比较贫瘠,土壤里的沙子含量较多,最令我们不满意的是这块菜地比较远,在村头那棵千年古樟边上。
刚开始,我和小罗都怀着几分新鲜感,每天收工回来,会趁着暮色,担着粪担来菜地浇浇菜,慢慢地便有些厌倦,特别是到了冬天,天黑得早,山里又冷,我们就不太情愿去那块在我们看来有些遥远的菜地了。我和小罗就如同两个不愿抬水的和尚,收工回到家就东倒西歪懒懒散散的。小罗比我好一点,他是家里的老大,会做菜,家庭条件也比我好,时不时会掏出一个鸡蛋来变着花样。而我往往对付一餐算一餐,实在变不出法子了,我就把中午吃剩的菜汤留着,晚上掏饭再将就着吃一餐。
好在这样的苦日子没过多久。房东大嫂隔三岔五地让读四年级的红花给我捧菜肴过来,并且还烧土豆炒薯藤地不断翻新着碗中餐。我有点不好意思,特地用油票去供销社的小店里买了半斤菜油给房东大嫂送过去。却被她数落了一番:“你可不敢和我这样客气。给你的那点,我在食锅里多放一瓢就是了。”
寒冬里的某个黄昏,我们几个知青在石井村参加完每月一次的学习日学习,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回村。暮霭四起,夕阳的最后一抹暖意已被群峰吞没,朔风吹来,飕飕如刀。我不禁打了个寒颤,却分明看见不远处有两位壮汉,一前一后分别挑着粪桶,手持担柱,往山腰间攀行,担上的粪桶随着他们吃力的步伐左右摇晃着。这时,前面那位已小心翼翼地放稳担子,正用木勺为地里的青菜浇肥,小罗一边竖起衣领一边对我说,“这种鬼天气在这种鬼地方拨弄几棵青菜,真是不容易。”我突然认出,那位正在浇肥的壮汉,是我的房东大哥。
看着房东大哥的身影,我不禁想起红花捧着菜的样子,想起房东大嫂的笑容,想起古樟树下的那块菜地……
自那以后,不管有多劳累,我收工后回到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挑起粪桶去村头浇菜。虽然我种的菜看上去总是面黄肌瘦的模样,远没有房东他们种出来的有那种肥头大耳的富贵相,但伴着我过平常日子已不成问题。
三
隐将人水稻田不多。每个小队仅有十几亩沿山湾而筑高低错落的梯形水田,单块田的面积都不大。我第一次耘田那天,小队长王大伯把我带到一小块梯田前,说是把这块田耘完算我半天的农活,吩咐完耘田的要领后他就离开了。我看着这块田比房东家的客堂间大不了多少,队长让我半天干完,我知道他是在照顾我。
六月里的天空像一口烧红的铁锅,烈日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,仿佛将水田蒸煮成一汪沸烫的泥潭。我赤脚踩在水田里,就像置身于热锅里,汗水早已浸透了衣衫,从额角滚落的盐珠混着泥点溅进眼睛,刺痛得让我睁不开眼。最让人难以忍受和惶恐的,是那些隐藏在水田里的蚂蟥,它们像发起总攻的千军万马一样,从四面八方的田水里扭动着黑褐色的身躯迅速向我包抄过来,我立即感到了一双小腿上难忍的痛痒,便逃上田埂捉蚂蟥。谁知那些蚂蟥异常贪婪,即使被拉断了身躯,它的头部仍然像是嵌在我的腿肉里叮咬,这让我毛骨悚然。
“被蚂蟥咬住了不要硬拔。”我抬头一看,不知什么时候,王大伯的三儿子三华来到了我跟前,他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小布袋,从里面抓了一小撮盐,往我腿上的那些蚂蟥搓了搓,然后取出腰间的柴刀,用钝的那头敲打着我的腿肚子,果然,那些蚂蟥纷纷脱落坠地。
三华比我大两岁,皮肤黝黑,为人憨厚。他脱下自己脚上穿着的长筒胶鞋,执意让我穿上。我说,这鞋还有吗?他笑道,我皮肤又厚又糙,蚂蟥咬不进去。
我穿上长筒胶鞋后站在水田里,就像身在碉堡的哨兵一样有了安全感。在三华的帮衬下,我们很快就把这块田耘完了。我如释重负地上了田埂,赶紧去树下猛喝几大口清茶,却见三华在田的那头,不停地用柴刀敲打着小腿肚子,我走过去将茶葫芦递给他时,发现他那黝黑的小腿上血迹斑斑。他看我过意不去的样子,一边喝着清茶一边笑呵呵地说:“没事的,回去后捣点紫草叶,用捣出的汁液抹上,马上就好了。”
四
由于田少,大米对隐将人来说是稀罕物,也是奢侈品。一般都用于过年过节的打年糕或是裹粽子。他们常年的主要口粮是玉米,当地话叫做“苞糯”。隐将人一般早晚都吃苞糯糊,中午吃苞糯粿(饼)。我刚开始对天天吃这个东西有些不习惯,后来适应了,慢慢地感觉到苞糯确实是个好东西,特别是苞糯粿,烹制方便,只需烧菜时,在铁锅上端贴上三四张巴掌大的用苞糯粉和水伴成的饼,锅中间的菜熟了,苞糯粿也可以铲下来吃了。考究一点可以做成菜粿,以腌菜、豆腐等做馅,吃起来糯口鲜脆。苞糯比大米耐饥,还特别适合作野外干活时的干粮,只要拣几根柴火燃一堆火,围着火烤几张苞糯粿,然后用辣椒酱或是豆腐乳抹在苞糯粿的表面,酥香可口,四五张粿下肚,再喝上几口清茶,保管到歇工前不会肚饿。老一辈的隐将人常说:“脚踏白炭火,手捧苞糯粿,除了皇帝就是我。”
苞糯虽然没有水稻那般难伺候,但也绝非“省油的灯”。隐将多山地,但家门口的熟地也不多。隐将人每年开春前会去偏远处觅一片灌木杂草丛生的山坡,用原始的刀耕火种办法,把杂木丛和乱草伐去,烧成草灰作肥料,开春后寻个日子,最好等到一场春雨下过,村民们再上山,用小锄掘出一个个浅坑,撒上苞糯种子。
苞糯苗开始分蘖时,要过来锄一次草。这种刀耕火种开辟的地方一般都比较陡峭,与悬崖为伍。所谓锄草,其实是徒手拔去苞糯苗四周的杂草。为了防止滑下山崖,有时需要我们一手抓住身旁的野藤之类,但挨着的一些荆棘和带刺小植物,会把手掌扎出血来,更让我心惊肉跳的是,有些草叶背面隐藏着一些毛很粗很长的毛毛虫,一有碰触皮肤就立马红肿起来,比蚂蟥的叮咬疼多了。
立秋以后,苞糯杆怀中的苞糯棒长成胖娃娃模样,让人看着欢喜,但是烦恼也跟着来了,野猪会窜出来拱断苞糯杆,偷吃“胖娃娃”。这些畜生也怕人,往往会在夜间出来兴风作浪。看上去齐刷刷的一片苞糯地,有时隔天就会大半东倒西歪,狼藉不堪,残缺的“胖娃娃”散落一地,让人心疼不已。
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,小队里派人在苞糯地里就着地势搭起简陋的竹棚,每夜派人看守。
一个雨后的傍晚,我们三小队的副队长方老汉,带着我和小罗来到一片崎岖的山坡苞糯地,苞糯地的周围是密匝匝的杂木林,竹棚搭在苞糯地中间凸起的岩石边,视线很好。我们像阵地上的战士一样,在战壕里摆放好打仗的武器弹药:猎枪、手电筒、铜锣、铜钹等等。
一阵秋雨一阵凉。天黑后,山风卷着残叶掠过竹棚,寒意像一张无形的网,将整个苞糯林裹得冷飕飕的。方老汉在竹棚旁燃起一小堆篝火,为御寒,也为壮胆。夜色如墨,除了火丛映照的一小圈飘忽不定的光亮,四周看不清任何东西。整个山坡死一般的寂静。我用手电筒四处照射,笔直的光束在苞糯地里穿插着,可以看得出苞糯杆上的叶片被雨水洗得亮闪闪。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和苞糯的甜香。
方老汉让我们不要太紧张,说前半夜应该没啥情况,催我和小罗先打个盹。我靠在竹棚上,虽然闭起眼睛,但毕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狩猎般的新奇,难免有些紧张和兴奋,脑子里东想西想,一时难以入睡……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,正当我恹恹欲睡时,方老汉摇了摇我的肩膀。我听到苞糯杆丛中传来一阵剧烈的窸窣声,由远及近,像是有沉重的躯体在湿漉的苞糯地里慢慢移动。方老汉打开手电筒朝声响处照去,只见一头壮如小牛的野猪,贪婪地啃着被它拱在地上的苞糯,身边躺着横七竖八的苞糯杆。那畜生并不怕光,只是稍微一愣便镇定下来,一边啃着苞糯一边对峙着,它的喘息粗重而急促,夹杂着低吼,獠牙在灯光下闪着寒光。
小罗赶紧抓过猎枪交到方老汉手里。方老汉却急忙说道:“快,敲锣!”我和小罗赶紧操起铜锣和铜钹,咬紧牙关一阵猛敲猛打,“哐哐哐”!“呛呛呛”!震耳欲聋的声音骤然撕裂了宁静的夜空,在山谷里回荡。那头野猪受了惊,仓促地低吼着调头,消失在苞糯丛深处的黑暗里。
锣钹停敲后,黑夜恢复了平静。我立即感到手麻和耳鸣。我问方老汉,刚才为什么不用猎枪打野猪?方老汉挥了挥手说:“使不得,打野猪是有风险的。十多年前,也是守苞糯,就是因为没有把那头大野猪一枪打死,被奔过来报复的野猪用长长的獠牙拱去我半边屁股。亏得我当时头脑还拎清,赶紧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装死,要不,那头受伤的野猪肯定会要了我的命。”方老汉说着站起来用手轻轻拍着自己的右边臀部。我这才发现,他右半边臀部的裤子里果然是空荡荡的。方老汉的脸上仍挂着一丝余悸,说:“不到万不得已,是不能开枪的。”
我和小罗不敢再怠慢,每过一刻钟左右便使劲敲一次锣和钹。天蒙蒙亮时,我俩竟在疲倦中睡去,等我醒来时,天已大亮,我发现方老汉手持猎枪,两眼炯炯有神地向四周扫视,像一位严阵以待的哨兵。
早饭时间,我们烤起了苞糯粿,兴许是饿了,这抹了辣椒酱的苞糯粿味道与以往大不相同,吃起来特别香酥过瘾。我正品尝着手中的美味,小罗却推推我的肩膀,示意我看身旁的方老汉,只见方老汉手里拿着苞糯粿,倚靠着竹棚酣然睡去。
五
隐将人的稻米和苞糯加起来,也只能维持大半年的口粮,还有小半年是需要买粮食吃的。幸亏山上宝物多,隐将人靠山吃山,能够变钱的经济作物有茶叶、山茱萸、山核桃等等。隐将人的茶叶产量并不多,基本用于自家泡清茶。
山茱萸确实是隐将一带的特产,即使在附近的其他山村也很少见到,当地俗称“红枣皮”。“红枣皮”的树型很好看,有点像樱桃树,只是比樱桃树略矮小,但树冠更张开些,叶子也小些,果子呈枣红色,像枸杞,又比枸杞圆一些。果子摘来后用水煮过再挤去内核,晒干后卖给供销社。据说“红枣皮”是制中药的良品,有健脾补肾的功效。收购的价格要比山核桃贵许多,可惜产量远不如山核桃。
说起山核桃,隔壁临安的名气要大得多。但房东大哥却告诉我,其实临安山核桃品质并不如我们的,他们只不过离杭州近,懂得城里人口味,比我们会加工。到了隐将我才知道,山核桃打下来后,除去皮后需要用水煮一整夜,火候不到核桃仁就会有涩味。房东大哥说:“你想,临安人山核桃比我们多,但柴火比我们少,煮的时间不够,吃起来麻口。”
我们到隐将的那一年,正遇山核桃大年。那是我第一次认识长在树上的山核桃。青青的卵圆形果实挂满了枝头,大都两三成簇,随山风摆动碰撞,发出沙沙细响。
我们小队里有位名叫章寿财的,是个哑巴,三十几岁了仍是单身,很聪明,也很壮实,干农活儿是一把好手,爬起树来像猴子一样灵光,据说是位打山核桃的高手。他每次在山核桃树下遇到我们知青,总是兴高采烈地指指树上的山核桃,然后张开右手掌做个倒挂动作,边比划边“哦,哦,哦”地发声,意思是今年的山核桃长得特别多。我们都非常喜欢他,经常学着他的样子,和他打哑语开玩笑。
“白露到,核桃撑破肚;竹竿摇,满地金,扁担挑。”白露刚过,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山核桃大战在隐将村拉开序幕,这时全村的男女老少会暂时放下其他活计,学校也会放农忙假,全力以赴收获这全年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天色刚呈鱼肚白,我就挎着柴刀背着布袋地全副武装,跟着小队的打山核桃大军出发了。壮年男子背着十多米长的竹竿,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队伍前面,后面是挎着竹篮、背着和拎着各种布袋的女人、老人和小孩。
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,来到一片山岭。几天前我跟着三华他们等十多个人来过这个地方,那次是做山核桃开打前的准备工作:用柴刀把山核桃树下那些小灌木、杂草理干净。这才四五天时间,可以看见那些被柴刀劈过的地方又冒出一些新茎来。这片山岭既偏僻又陡峭,已呈黄绿色的山核桃挂满了枝头——山核桃树很怪,越是长在陡峭地带的越会结果实。这时,天色已大白,整片山核桃林在朝阳的映照下,山岭被染成金黄色。
壮年男子纷纷攀上十多米高的山核桃树,脚踩虬枝,挥动长杆对准挂果枝头“梆梆梆”地敲打起来,黄绿色的带皮山核桃顿时如冰雹般坠落,撞击在枝叶上发出“噼啪”的脆响,黄绿色的“冰雹”也会经常砸在我们这些拣山核桃人的身上,虽然有些疼,但仍然开心,毕竟都是丰收的果实啊。
陡峭山地的山核桃是最难拣的,从树上坠落的山核桃会直接掉进岩缝里去,有些则会顺着山势滚出去很远。掉进杂草里的那些不好拣,因为这些杂草叶上往往附着当地人称为“刺蟊”的毛虫,身小毛长,呈绿色,毒性强。
我没拣多久,右手指尖就触到了“刺蟊”而红肿起来,感觉就像蜂蛰一样痛。从山核桃树上一跃而下的章寿财看到了我的情况,示意我不要着急,他随手拣起一颗饱满的带皮山核桃,放到嘴边用牙齿咬下一大块绿皮,把它在我的伤口来回摩擦敷设,比划着手势告诉我,这样可以止痛。我闻到了由绿皮散发出来的苦涩味儿。过了一会,手指的疼痛果然好了许多。
我见章寿财又要上树,便向他打着手势,请他教我打山核桃。他爽快地答应了,选了一棵矮山核桃树,站在地上手把手地教我。十来米长的竹竿握在手里伸出去,手感有些重,我没挥几杆就感到手酸了,而山核桃并没有打下几颗。章寿财用手紧抓我握杆的手,“哦哦”地比划着,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:挥杆的幅度不能太大,要使暗劲。根据他的指点,那些黄绿色果实在我的竹杆下也终于变成一阵阵坠落的“冰雹”。问题是,这种地面就能打的地方很少,在树上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何况,我还不会爬树。
半个月后,山核桃基本上都打完了,金果落尽后的山核桃林褪去往日的喧闹。千辛万苦收来的山核桃进入繁琐的制作流程,先用硬木制成的磨盘碾去山核桃的绿皮,剥出来的山核桃籽呈黄白色,隐将人称为“白籽”。将白籽挑出后放进大铁锅里水煮一个晚上,第二天把山核桃捞出,分批倒入一大盆水里,剔除浮在水面的空壳,然后再晒干。这时白籽已呈黑色,隐将人称之为“燥籽”。我们平时吃的山核桃都是由燥籽添佐料加工而成。
我很有成就感地背第一份“燥籽”来到供销社,收购人员将我的燥籽随意取出十颗,用榔头击碎,被告知有两颗是空壳,便将我的“燥籽”全部退回,这让我有些沮丧。他告诉我,按收购规定,随意抽查的十颗里,空壳不能多于一颗。我在房东的帮助下查出了原因,是我在浸水验空壳时没有将半沉半浮的挑出。有了经验后,我就让水多浸一会,尽量将那些快冒出水面“燥籽”也挑出,以后的“燥籽”都一次通过。我至今还记得,当时“燥籽”的收购价是每斤二角九分钱。
我那年分到了七十多斤“燥籽”,补贴我小半年的买粮钱是绰绰有余了。
六
两年半以后,我离开了隐将村去湖州读书。我在湖州的第二年秋天,三华邮寄了一小袋盐炒山核桃给我,并在包裹里附了一封信,告诉我今年村里打山核桃死了两个人,一个是石井村的,当场就没命了;另一个是哑巴章寿财,摔成重伤,几天后不治身亡。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章寿财在山核桃树上那生龙活虎的身影,不禁热泪盈眶,怔怔地望着眼前那袋山核桃,半晌回不过神来。
后来,房东夫妇去县城居住,我就很少回隐将村了。然而,我经常在梦里回去,梦见我熟悉的山村,那些熟悉的山和水,那些熟悉的人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