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![]()
![]()
晒 秋
○ 谷子
霜降过后,进入深秋,心里头便仿佛也铺开了一片暖洋洋的秋光,那些蛰伏在记忆角落里的、关于晒秋的零碎光影,竟都活泛起来,争先恐后地要挤到眼前来。我的脚步,便不由自主地,向着郊外那疏疏落落的、还保留着几分旧时风貌的村落走去了。我要去寻一寻那晒在日头里的、完整的秋天。
乡村的路是渐渐窄了,尘嚣也渐渐远了。待到一座小小的石桥横在眼前,桥下是几近干涸的、露出圆润的水码头石。我便知道,是到了村里,村子是静静的,像一位在秋阳下打盹的老人,安详得叫人不忍高声。我们苏北老家家家户户的屋舍,并无婺源那般粉墙黛瓦的雅致,却多是些朴拙的、带着泥土本色的平房或“七字型”楼房,院墙也歪歪斜斜的,垒着岁月的斑驳。然而,正是这朴拙,那满院都铺满秋光最好的底色。
瞧!那一片一片的金,是玉米铺成的。饱满的棒子,被灵巧的手剥去了外衣,露出齐整整、黄澄澄的牙,密密地摊在苇席上,或是直接倾倒在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场上。阳光照下来,每一粒都像是一个小小的、吸足了光的“黄金”,亮晶晶的,仿佛能听见里面阳光流淌的、静谧的声音。那一片一片的红,是辣椒织就的。有整个儿串起来,挂在屋檐下、墙头边的,如一挂挂等待燃放的、沉默的爆竹;也有细细切碎了,在巨大的竹匾里摊开晾晒的,那红便不是一整片的了,是碎碎的,洋洋洒洒的,像哪个淘气的仙人打翻了胭脂盒,又像是一片流动的、炽烈的火,要把这秋天的微凉都给暖热了。
还有那褐色的干豆角,弯弯扭扭的,像是写满了农家故事的象形文字;那白色的萝卜条,肥腴腴的,被切成匀称的长条,一丝不苟地排列着,像是待检阅的士兵;更有那悬在廊下的,一串串的腊肉、咸鱼干,经了秋风与阳光共同的抚弄,透出一种半透明的、沉甸甸的赭红色,油汪汪的,散发着一种踏实而诱人的香气、允诺了冬日温暖的承诺。
深秋的乡村游,我静静地站在一户人家的院外,隔着低矮的土墙向里望。一位老妇人,头上包着蓝布巾,正佝偻着身子,用一把木耙,细细地翻动着匾里的辣椒碎。她的动作是那样迟缓,却又那样富有韵律,木耙过处,那一片红便漾开微微的波纹,随之升腾起来的,是一股辛烈而醇厚的香,直往人鼻子里钻。她没有看见我,仿佛整个天地间,只剩下了她,和她那一场地的红色辣椒。阳光勾勒出她银发的轮廓,也把她那双布满老茧、深如沟壑的手,照得清清楚楚。那双手,是创造这一切斑斓的、最原始的写意画。
看着看着,我心里忽然漫上一股无端的、温柔的惆怅。这满院子的丰饶,是何等的喧嚣,何等的热烈;然而,守护着这喧嚣与热烈的,却是这般古老的、近乎永恒的寂静。这寂静,是属于土地的,属于季节的,也属于这老妇人一样的、无数代农人的。他们不言不语,只将一年的辛劳、期盼与喜悦,都托付给这无私的秋阳,静静地晒着。这晒的,哪里仅仅是物呢?这分明是在晒日子,晒那一个个春耕夏耘、秋收冬藏的日子;是在晒生命,晒那与土地纠缠一生、终于得来的、沉甸甸的生命的结晶。
我的思绪,便不由得飘得更远了。我想起古人的诗句来了。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唯落晖。”王绩眼中的秋色,是疏阔的,是带着一抹斜阳的、淡淡的哀愁的。那秋色,是属于士人的,是望远的,是抒怀的。而眼前这农家的秋色,却是如此的具体,如此的密不透风,它不给你伤感的余地,只用最实在的色彩与香气,将你包裹,告诉你生活的本质就是这般朴素而强烈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秋天。一种,是看的;一种,是过的。
徘徊间,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更为古老、也更为恒久的画卷。在刀耕火种的年月里,当第一粒多余的谷子从先民的手中滑落,那智慧的灵光便也如这种子一般,落入了心田。他们抬头,望见了那慷慨的、无穷无尽的太阳。于是,晒,这最原始也最伟大的贮藏方式,便开始了。平原之上,可以席地而晒;而在南方的山区,平地是金贵的,人们便向空中索要空间。于是,屋顶上支起了晒架,窗台外探出了晒盘。自此,这晾晒便不再仅仅是土地上的平面铺陈,而成了一首立体的、攀援而上的田园诗。春晒山笋与春茶,那是一抹清新的绿意;夏晒瓜茄与豆角,那是满眼的油碧与浅紫;到了秋,便是这黄豆、玉米、稻谷与辣椒的、金与红的主场;便是入了冬,也还有腊肉、咸鱼与干菜的、深沉的赭褐与霜白。一年四季,光阴的流转,就这样被具象为屋檐下、晒架上不断更迭的色彩。这“晒秋”的“秋”,原来早已超越了时令,它泛指了一切需要阳光来封存的生命,是一切收获的代称。这名字起得真好,一个“晒”字,是动作,是过程,充满了劳作的动感;一个“秋”字,是结果,是意境,弥漫着圆满的静美。这盛典,是华夏子孙共同的节日,却又因了这广袤土地的不同禀赋,而演出了南北各异的风情。

南方的晒秋,我是熟悉的,一如眼前所见。它以江西婺源篁岭为最,那真是将生活过成了一幅画。想象那景象:数百幢徽派古居,依着山势,层层叠叠地攀升上去,直如“梯云人家”。秋日朗朗,家家户户将那硕大的竹匾托出眺窗,架在晒杆上。辣椒的红,玉米的黄,菊花的白,南瓜的橙,在那黛瓦粉墙的映衬下,被这立体的梯田式布局一衬托,哪里还是寻常的农事?分明是上天遗落在此的、一块巨大的、活生生的调色盘了。那是一种极致的、近乎炫耀的美丽,是把丰饶当作艺术来供奉的、精致而用心的排场。
而北地的晒秋,我虽未曾亲见,却从旁人的描述与文字的记载里,能想象出另一番况味。那里的晒,少了几分装饰性的绚烂,却多了几分应对严酷自然的、沉雄的实用主义。当秋风开始捎来西伯利亚的寒讯,人们便要为那漫长的、白雪覆盖的冬天做准备了。他们的晒秋,是一场更为严肃的、关乎生存的“战备”。大白菜要成堆地码起来,萝卜要切成条或旋成花,用盐杀去水分,一串串挂在院中,像待命的兵士;硕大的葫芦,能“旋”出数米长的细条,垂在长竿上,仿佛待奏的五线谱。就连那滨海的人家,也在滩涂上支起长长的竹架,将开膛破肚的带鱼、鲅鱼、黄花鱼,密密地挂上去,远远望去,银白一片,竟有“沙场秋点兵”的雄壮。北方的晒秋,是把生活的艰辛与韧性,都晒在太阳底下了,那场景,朴拙,豪迈,自有一股动人的力量。
想着这南北的差异,我忽然觉得,这晒秋的景象,竟像极了我们这民族的内里。有精雕细琢、富于诗情画意的一面,如同我们苏北地区的庄户人家;也有脚踏实地、在严酷中求生存的、坚韧不拔的一面,如同那院落里挂满的山芋干、萝卜干、红辣椒与干菜。这秋色的画景,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全部真相。
日头渐渐偏西了,光线变得愈发柔和,像一块融化了的、温润的琥珀,涂抹在院子里所有的物件上。那原本有些刺目的红与黄,此刻都沉静了下来,泛着一层暖暖的、旧旧的光泽。空气里的香气,经过一整日的蒸腾,似乎也愈发地醇厚了,不再是单纯的蔬果之气,而是混合了泥土、阳光、岁月以及人烟的一种复杂的、让人安心且眷恋的“人世间”的味道。我悄悄地转身,循着来路回去。那老妇人依旧在院子里忙碌着,她的身影在斜阳里被拉得长长的。我什么也没有买,却觉得行囊是满满的,心里是满满的。我带走了满眼的色彩,满鼻的香气,和满心的安详。
回到书斋,已是暮色四合。推开门,那股熟悉的、带着纸墨与尘埃的阴凉气息扑面而来。我却没有立刻开灯,只静静地坐在昏暗中,让方才在村子里汲取的那一腔秋阳,在身体里缓缓流淌。窗外,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,是另一种星辰,另一种繁华。但我知道,在那灯火照不到的、广袤的乡野里,此刻定有无数个如我所见的院落,正收敛起它们一日的斑斓,在星月之下,静静地等待着又一个黎明的曝晒。
这晒秋,它晒的,是春播时手心的汗,是夏耘时脊背的霜,是望穿秋水时的焦灼,是颗粒归仓后的心安。它把无形的劳作,晒成了有形的色彩;把流逝的光阴,晒成了可以贮藏的滋味。它是书写在大地上的、最朴素的诗,是农人献给岁月、也献给自己的一首无言的、盛大的颂歌。
晒秋这首颂歌,年复一年,在秋风起时准时唱响,唱给懂得它的人听。晒秋不是炫耀,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,农人们用勤劳的双手,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晒秋的过程,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写照。晒秋,不仅是一种传统习俗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晒秋,不仅晒出了丰收的果实,更晒出了农民们对自然慷慨馈赠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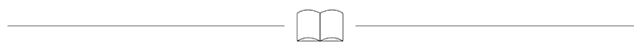

(谷将,笔名:谷子,江苏盐城人,久居射阳。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,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。四十余年来,著有诗词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随笔、杂文、论文千余篇,近300万字;出版诗歌集《站在时光的渡口》、诗词集《诗路辙痕》两部;散文集《边走边悟》《湿地守望》《湿地册页》三部;书法作品百余幅,作品多见于各级报刊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