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![]()
入诗入画的那场雪
○ 何其敏
是那一声不知从岁月哪一处褶皱里漏出来的吟哦,先于眼前的景象抵达了我的耳畔——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。杜甫的句子,在这山下的平野间蛰伏了千年,此刻却像一枚被体温捂热了的玉,忽然有了生命,带着唐时的霜气与苍茫,铮然作响。我们文友仨便是在这诗句的余韵里,让车子划开冬日清晨薄薄的曦光,向着那片被传说与洁白重重包裹的秘境驶去。心里痒痒的,仿佛不是我们去寻雪,倒像是那场预约了千年的雪,正通过一句诗的召唤,等着我们在2026新年元始的赴约。
嗨,天道有情,透过车窗就看到了雪景……那窗外的景致,由平铺直叙的田畴村落,换成了层层叠叠、欲说还休的山的屏风。绿意先是沉郁的,是蜀地冬日不肯褪尽的一件旧袍子;继而,那绿上便敷了一层淡淡的、似有还无的灰白,像是美人晨起未及梳洗的倦容。再往上,这倦容便成了真正的素面——一抹惊人的、毫无杂质的白,陡然从山脊的那一面漫溢过来,不由分说地占领了所有的视线。那白,不是死寂的,而是含着光的,温润的,蓬松的,让人疑心是天上宫阙的棉絮库房倾倒了,又或是一整个春天的梨花,被一只无形的手一夜之间冻在了枝头,汇成了这浩瀚无边的香风雪海。
我们的车,便像一叶小心翼翼的黑舟,滑入这片凝固的、柔软的海洋。雪是这两日落的,据说是今冬的首降,分量足得让山也显出了臃肿而憨拙的体态。道旁的松与杉,成了这阒寂乐章里最沉默的音符。它们的枝桠承托着过于丰厚的馈赠,低低地垂着,形成一道道雪的门拱,或是素白的穹顶。偶尔有那不堪重负的,“噗”地一声,一团雪便从高处坠下,在下方扬起一阵轻烟似的雪雾,那声音闷闷的,绒绒的,像是大地的一声满足的叹息。除此之外,便只有我们轮胎碾过新雪那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清亮而又结实,是这静穆世界里唯一的、带着人迹的节奏。
终于到了半山一处开阔的坪台。我们迫不及待地投身于这片白色王国。脚下是厚厚的雪毡,每一步陷下去都发出欢悦的呻吟。我俯身捧起一掬雪,那凉意是尖细的,瞬间刺透手套的纤维,直抵指尖,却又奇异地不让人觉得痛苦,反倒是一种提神醒脑的清澈。细看那雪粒,并非想象中的六出菱花,而是细密的,仿佛被谁精心研磨过的水晶砂,在透过云层的天光下,闪烁着无数针尖似的、不肯安分的星芒。
我们向更高处漫步。老刘,我们中最富史学癖的,且特别酷爱拍摄风物。他忽然指着远处一面陡峭的、覆着皑皑白雪的巨崖,喃喃道:“你们说,一千二百多年前,杜甫所见的可是这一片山?他诗里的‘窗’,又在何处呢?”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心湖,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,那悬崖壁立千仞,雪色在阴影处是沉静的蓝灰,在受光处则是耀眼的银白,纹理纵横,宛如天神以雪为墨、以山为纸挥就的一幅狂草。

时光的鸿沟仿佛瞬间被这无差别的雪抹平了。我几乎能想象,在某个清冷的成都清晨,诗人推开他那并不轩敞的草堂木窗,猛一抬头,这西岭的雪顶便如此邈远而又如此确凿地镶嵌在窗框之中。那“含”字用得真妙,不是“对”,不是“望”,是“含”。窗子像天地间一只沉静的眼,将那片永恒的寒凉与皎洁,温柔地含在了口中,也含进了后人无数个眺望的梦里。
这眼前的雪,便不再是地理的雪了。它成了时间的化石,是唐朝的一片未曾融化的月光,是杜工部掷向历史长河的一枚清响的韵脚,此刻,正被我们这几个冒昧的后来者踏在脚下,捧在手中。这感觉奇异极了,我们是在赏雪,又仿佛是在与一个浩大而古旧的灵魂,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。
下得山来,寻到山脚一家小小的茶馆歇脚。店家在檐下生了红泥小炉,煮着一壶老荫茶,氤氲的热气与清冷的雪气纠缠在一起,别有一番滋味。我们捧着粗陶碗暖手,身上的寒气一丝丝被逼出来。话题自然还是离不开那场雪,离不开杜甫。
老李,平日里最是散淡风趣的一个人,抿了一口茶,笑道:“我看那雪,厚得能埋下半部唐诗。咱们踩过的,说不定就是王维的‘空山新雪’,岑参的‘忽如一夜春风来’,或者是柳宗元那孤舟边‘独钓’的寒江雪呢!”这话引得我们都笑了。笑声落在雪后的空气里,显得格外清亮。他又指着窗外一株枝条遒劲、雪挂玲珑的老梅,说:“这梅,倒像是从杨万里的诗里伸出来的,‘玉雪为骨冰为魂’,只是不知它有无‘诗翁’在傍,为它‘捻断数茎须’了。”
我听着他们的谈笑,目光却再次飘向窗外。暮色正从四面的山脚缓缓升起,像一砚渐次化开的淡墨。天空是那种冷冷的鸭蛋青色,而西岭的雪峰,在渐暗的天光里,反而更加醒目了,呈现出一种幻梦似的、非人间的皎洁。它静静地卧在那里,仿佛一头安详的、沉睡的巨兽,皮毛是世界上最光滑的银缎。白日里游人留下的些许痕迹,此刻都被这宏大的暮色与雪光无声地吞噬、净化。山又恢复了它本初的、洪荒般的寂静与完整。
这时,我突然明白了杜甫那句诗的力量。它不仅仅是一个画面,更是一种姿态,一种心境。那扇“窗”,是有限对无限的凝望,是瞬间对永恒的捕捉,是喧嚣人世对静穆自然的一瞥惊鸿。我们今日的驱车百里,踏雪寻幽,不也正是为了在自己生命的“窗口”,觅得这样一片可以“含”在心中的“千秋雪”么?它未必是地理的风景,而是一种精神的映照,一种在烦扰日常之上永远存在着的美与辽阔的启示。
归途的车启动了。我最后一次回望。西岭的雪影在越来越深的夜色里,渐渐淡成天幕上一抹幽微的、却难以磨灭的亮痕,像一帖年代久远的诗笺,墨色已褪,风神却永驻。车窗外,是流动的、模糊的黑暗;而在我心的窗格里,却已然含住了一片清凉的、亘古的雪光。这一日的奔赴与浸染,仿佛只是为着验证,那千年前的诗人未曾说谎——那雪景真是太美了,它的美却能穿越时间的风雪,抵达后来者的眼与心,既入诗,亦入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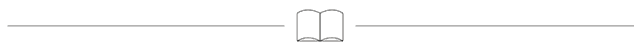

(何其敏: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,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,先后在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中国妇女报》《新华每日电讯》《南方周末》《四川日报》《滇池》等报刊,发表游记、散文、纪实报告文学等作品上千篇,计200多万字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