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![]()
迟 雪 纪
○ 吴钊同
天空是一种均匀的铅灰色,沉甸甸地压在北京城的屋檐上。可家乡新疆的雪从不这样预告自己——它们总是突如其来,带着帕米尔高原的凌厉,在刹那间席卷天地,将戈壁、白杨和葡萄架统统纳入同一片凛冽的洁白。那里的雪是宣言,是判决;而这里的雪,还在犹豫。
第一片雪花落下时,我几乎要错过它了。那么缓慢,那么迟疑,仿佛在穿过一层层看不见的阻力。雪打在羽绒服上发出簌簌的轻响,这声音与新疆不同。故乡的雪落下时是干燥的沙沙声,这里的雪却是湿润的,带着某种黏着的温柔。
这让我忽然意识到:在北京,雪是节日;在新疆,雪是日常。日常不会被凝视,不会引发惊喜,它只是存在,像呼吸,像昼夜交替。而此刻,这片我见过千百次的白色,因为空间的位移,竟然变得陌生。
雪花落在我的睫毛上,我静静地感受,冰凉的触感让我闭上眼睛。我想起阿尔泰山脚下的冬牧场,雪深及腰,天地间只有风和羊群踩雪的声音。那种寂静是有重量的,它压迫着胸膛,也澄清着思想。而此刻北京的雪声是温和的背景音——远处隐约的汽车鸣笛,近处学生的笑谈,雪花本身反而成了这城市喧嚣的消音器。
我继续走着,雪在脚下发出咯吱的声响。这声音比新疆的雪沉闷些,许是混杂了太多这座城市的气息:昨日的尘埃,匆忙的脚印,无数故事的残片。一片雪花恰好飘进我的衣领,在脖颈处融化,那一线凉意让我打了个激灵。这具十九岁的身体里,还住着那个在零下三十度天山脚下雪堆上打滚的少年,他的记忆正在与此刻的感受对话。
情人坡路边长椅上的雪已经积了薄薄一层。我拂去一片坐下,看雪如何耐心地覆盖这个世界。它掩盖了枯草的凌乱,模糊了石阶的棱角,把自行车棚的锈迹变成柔和的轮廓。雪在施行一种温柔的专制,它不摧毁,只是暂时地修改,给予一切事物第二次呈现的机会——以纯洁的名义。
我突然理解了这种陌生的感动从何而来——在北京,雪是异乡人;而我,也是。我们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偶然相遇,彼此辨认出了对方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疏离。新疆的雪是我的一部分,像我的口音,我的记忆;而北京的雪是一面镜子,让我看见自己如何站在两种生活、两种冬季之间。
这场雪不会改变什么——明天它或许就会消融,露出北京原本的样貌。但此刻,它存在着,以最轻盈的方式占据着时间和空间。而我,一个见过更大风雪的新疆人,正为这场温和的降雪感到一种近乎荒谬的触动。
或许成长就是如此:我们带着故乡给予的尺度去丈量世界,却发现最深刻的测量往往发生在内心。新疆的雪教会我坚忍,北京的雪却让我看见坚忍之下,那些从未言说的柔软。雪还是雪,不同的是凝视它的眼睛,和眼睛后面那个正在蜕变的人。
在雪与视线的参差中,我想起加缪写过的句子:“在深冬,我终于发现,我的心里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。”
而此刻在我的夏天里,正落着一场安静而陌生的雪。它不带来寒冷,只是轻轻覆盖,轻轻提醒:所有远方终将变成故乡,所有故乡都曾是远方。在这永恒的回环里,我们走着,看着,记得着——像第一片雪花记得天空,像最后一片雪花记得大地。
而这,或许就是全部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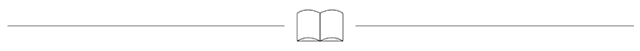
(吴钊同:清华大学未央书院2025届学生。高中期间曾多次获得“语文报杯”中学生主题征文全国金奖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