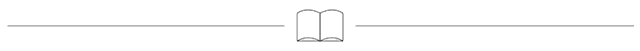![]()

星空下的野鹿荡
○ 谷 将
深秋时节,我踏上去大丰野鹿荡的路途。在那条羊肠而松软的小路上行走,才真正看清和理解这原始的野鹿荡的份量。
这是一条必须用脚步去丈量,用身体的倦意去换取亲近资格的羊肠小路。路是土路,被经年的风与长年的雨水弄得松软,走在上面,听不见像城市道路上行走声里那种焦躁的、硬底的响动,只有一种陷下去的、闷闷的声响,像是大地在以一种古老的语言同你低声寒暄。路的两旁,乃至目力所及的整个湿地,都被一种无边无际的、黄褐色的苍茫所占据了。那是芦苇,是茅草,是坦荡无垠的滩涂,它们以一种近乎固执的、原始的笔触,在黄海之畔铺开了一幅野性的画卷。这里没有江南水乡那种玲珑的、被精心梳理过的秀气;这里只有荒旷,只有一种不加修饰的、野性的力量,沉甸甸地压在游人的心上,也拓在游人的魂里。
海边的风是这里持久的主人。它似乎从没有片刻的停歇,掠过那无数已然干枯却依旧挺立的草尖,发出一种低沉而富有韧性的呼啸。这声音不尖锐,却绵绵不绝,仿佛一种永恒的叹息,又似这片土地沉雄的呼吸。你闭上眼,这声音便灌满了你的耳朵,将你从那个纷繁的、属于人的世界里一把拽出,放逐到这片湿地的荒野之中。空气里,是海水的咸腥、泥土的厚朴,以及腐草在水中缓慢分解所生出的、那种属于生命原初的、略带腥涩的气息。这气息不好闻,却也绝不令人厌恶;它太古老,太真实,直白地告诉你,生命的繁华与衰败,滋养与消亡,本就是这气息的一体两面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仿佛饮下了一杯酿了千万年的、粗粝而醇厚的酒。
我来此,是为了一个传奇,一个关于“四不像”的、麋鹿的故事。这念头,是我此行的目的。向导是老王,一位在这保护区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本地人。他的脸庞,是被海风与日光长久雕琢过的古铜色,沟壑纵横,每一道纹路里,似乎都藏着一段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。他不多话,只是默默地走在前面,脚步踏实而安稳,仿佛他本就是这土地生长出来的一棵会移动的树。他笑着,那笑容里有种见惯了来客好奇的淡然,指着远方,对同行的游人说:“野鹿荡在白天可以看见野鹿的行踪,其实,夜晚星空下的野鹿荡更加迷人。” 他的话像一粒石子,投在我原本只为麋鹿而设的心湖里,漾开了一圈新的涟漪。
走了一段路,见一处水洼塘。我于是俯下身去,顺着他指引的方向,去看那“微小”。那是一片不大的水洼,清浅得很,若非仔细瞧,水底是柔软的淤泥,衬得那水愈发澄澈。几只半透明的小虾,正一蹦一蹦地游弋着,它们的动作是那样纤巧而敏捷,细长的须子微微颤动,仿佛是在弹拨着看不见的琴弦。它们每一次的腾挪,都在那镜面似的水上,划出一环环极其细微、又极其完整的涟漪,一圈追逐着一圈,悠悠地荡开,直至消失在岸边。那姿态,像极了一场无声的、献给这片荒野湿地的芭蕾,极尽优雅,也极尽寂寞。岸边泥滩上,一个不起眼的小洞里,一只招潮蟹正举着与它身体全然不成比例的大螯,谨慎地探出半个身子,它的眼睛机警地转动着,打量着这个对它而言同样广阔无垠的世界。这一动一静,一水一陆,很是微小,却又精妙得宛若神迹。它们不像麋鹿那般拥有撼人的传奇故事,它们只是沉默地、坚韧地存在着,构成了这片巨大湿地最基础、也最不可或缺的脉搏。

这时,老王那带着浓重乡音的话又缓缓响起:“湿地啊!不只有大家伙。你看得越细,看到的生命就越多。” 我蹲在那里,忽然间像被一道光击中了。是啊,我一路走来,心里只装着那雄健的、传奇的“大家伙”,目光便也只习惯于平视与远眺,何曾想过要如此谦卑地俯下身子,去阅读这由微小生命写就的浩瀚“典籍”?这“看见”的第一步,原来不是昂首,而是俯身;不是猎奇,而是心怀敬畏的聆听。我恍然觉得,自己方才那一路的行走,竟有几分可笑的倨傲了。
黄昏,才是野鹿荡真正苏醒的时刻,是这出荒野戏剧的序幕真正拉开的时分。我们跟随着老王,隐蔽在一处观测点之后,像几个潜入者,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轻了。夕阳正在西沉,它将天边堆积的云彩,一点一点,染成了瑰丽而沉郁的橘红色,仿佛是上天打翻了一坛陈年的葡萄酒,那醇厚的色泽,恣意地流淌、浸润开来。广袤的滩涂,那原本黄褐的、有些寂寥的底色,此刻被镀上了一层温暖而神圣的金色,每一根草茎的轮廓都清晰起来,仿佛被一支无形的画笔精心勾勒过。
就在这时,远方树林的草丛开始晃动了。它们来了。先是影影绰绰的几个剪影,在芦苇的深处,若隐若现,像是从古老的壁画上走下来的精灵。然后,渐渐地,一群麋鹿,踏着沉稳而闲适的步伐,从那片金色的屏障之后,缓缓走了出来。它们的形体,比我想象中更要雄健、雍容。那一对对角枝,繁复地分叉、伸展,如同古时帝王冠冕上最华美的礼器,承载着一种不言自威的尊严。它们的躯体披着夕阳最后的余晖,皮毛泛着温暖的光泽,仿佛自身就是光的源头。那“四不像”的模样:角似鹿非鹿,头似马非马,身似驴非驴,蹄似牛非牛。此刻在我眼中,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,而是一种生命在漫长到无法想象的演化岁月中,被自然这只无形巨手精心塑造出的、独一无二的和谐。它们的存在本身,就是一种完美,一种打破了我们固有分类概念的、活着的奇迹。
我的目光,被其中一头雄鹿牢牢地攫住了。它离开鹿群,独自踱上一处略微高耸的土丘,昂起头,静静地眺望着这片属于它的、也包容着它的旷野。它的眼神,透过暮色,向我这边投来。那眼神里,没有惊恐,没有好奇,只有一种沉静到了极致的深邃。那眼神,仿佛能穿透千年的时光迷雾,与某个遥远的过去悄然相接。我忽然想起老王在路上告诉我的:就在一百多年前,这片广袤的南黄海湿地上,最后一只野生的麋鹿,已然在人类的猎枪与围剿中绝迹。眼前的这群生灵,是它们的子孙,是漂泊海外近一个世纪,作为“侨民”被小心翼翼地迎回故土的游子。它们站在这里,蹄下是祖先曾经奔跑、繁衍的土地,每一次呼吸,都带着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。它们的存在,本身就是一部沉默的、关于失去与回归、灭绝与重生的史诗。那雄鹿的眼神,哪里是鹿的眼神,那分明是一部镌刻在血脉里的、流动的史书。
它们开始低头,啃食着滩涂上耐盐的植物,主要是盐蒿。那“呦呦”的鹿鸣声,低沉而富有磁性,在黄昏静谧的空气里传得很远。它们的蹄子,偶尔踏入浅水,溅起细碎而晶莹的水花,那声音清脆,是这片荒野最动听的乐音。我看着它们,忽然明白了老王所说的“滩涂的王者”的含义。它们的蹄印,为更微小的生物制造出赖以存活的临时水坑;它们的粪便,无声地融入泥土,滋养着新一轮的生命循环;它们年复一年的迁徙与漫步,无形中塑造着湿地植被的分布与演替。它们不是这里的客人,它们是这里不可或缺的工程师,是这片土地沉默而忠诚的守护者。此刻,我“看见”的,不再仅仅是几头名叫“麋鹿”的珍奇动物,而是一个以它们为核心,由水、草、鱼、虾、蟹、微生物以及无数可见与不可见的生命,环环相扣、生生不息所编织成的一张完整的、湿地的生命网络。
最后一抹暖色的光,终于恋恋不舍地从大地的边缘隐去。夜幕,像一滴巨大的、浓得化不开的墨,从容不迫地降临了。也正是在这极致的黑暗里,星子,开始一颗、两颗,继而千颗、万颗地,在天鹅绒般的天幕上闪烁起来。野鹿荡因其远离一切城市的喧嚣,成为了观星的圣地。而此刻,我目睹的,是一场天地间最宏伟的交接仪式。

白日的王者们,那些麋鹿,在愈发深邃的苍穹下,化为了移动的、更加神秘的剪影。它们仿佛从现实的生灵,一步踏入了神话的领域。而头顶,是亿万年不变的、璀璨到令人心悸的星河。银河,那条浩瀚的光之河流,横贯天际,其间的星辰密密麻麻,仿佛天神洒下的一把无法计数的钻石尘埃,静静地燃烧,静静地流淌。这一刻,上下四方,古往今来,仿佛被压缩在了这同一个时空点上。那来自137亿年前的星光,无声地洒落在这些刚刚归家不过几十年的生灵身上,洒落在我这个过客的肩头。野性的呼吸与宇宙永恒的律动,在此刻达成了完美的和谐。这是一种震撼心灵的仪式,无需任何言辞与音乐,其本身的存在,便是一种直抵灵魂的、关于永恒的诘问与启迪。我感到自身的渺小,像一粒尘埃;却又感到一种奇异的宏大,因我的灵魂,此刻正与这麋鹿、这荒野、这星空进行着无声的交流,我仿佛也成了这广袤湿地与浩瀚星空存在的一部分。
回程的路上,万籁俱寂,只有那永恒的风声依旧,像是在为这片沉睡的土地唱着亘古的摇篮曲。我沉默地走着,来时那条松软的土路,此刻走起来,却觉得脚下坚实了许多。我的眼中,已不再看见荒凉;我的耳中,仿佛还能清晰地听见那群生灵在暮色中的呼吸,那沉静而有力的节奏。我眼中看见的麋鹿,已经升华为对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、对一段跌宕生命传奇的认知与敬畏。
星空下的野鹿荡,也在此刻,于我心中变得从未有过的具体而清晰。这清晰,是一种祈愿,也是一种确信。我愿这片南黄海的湿地,能永远如此刻般自由而野性,不被智能文明时代的巨轮所碾碎。我愿那麋鹿的嘶鸣,能永远如同这夜风一样,在黄海之畔回荡,成为这片土地不朽的魂灵。我愿每一个如同我一般来到此地的人,都能学会如何真正地“看见”:俯下身,看见渺小的伟大;抬起头,看见宏大的慈悲;在当下鲜活的生命跃动里,看见其背后沉甸甸的时光与责任。
我们看到的,哪里仅仅是鹿、是星、是荒野呢?我们看到的,归根结底,是“爱与责任”,是对这孕育了我们的、伤痕累累却又无比坚韧的母土的爱;这份责任是将这份原始的、野性的、壮美的诗意,完好地交到后世手中的责任。也只有这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”的古老诗意画卷,才能跨越千年的时光,永远在这片南黄海之滨的遗产地上,生动地、磅礴地演绎下去。那鹿鸣,是这荒野的心跳;那星空下,是我们不应遗忘的、共同的故乡。
![]()

(谷将,笔名:谷子,江苏盐城人,久居射阳。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,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。四十余年来,著有诗词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随笔、杂文、论文千余篇,近300万字;出版诗歌集《站在时光的渡口》、诗词集《诗路辙痕》两部;散文集《边走边悟》《湿地守望》《湿地册页》三部;书法作品百余幅,作品多见于各级报刊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