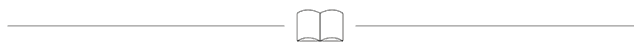![]()

![]()
恒 明
○ 吴钊同
那盏兔子灯,如今就挂在我宿舍的角落,兀自发着光。
制作是极其草率的——两块薄木片草草切割出兔子的轮廓,边缘还带着毛糙的木刺,前后蒙上印着兔子图案的布,中间塞进一串廉价的小闪灯,用粗糙的白纸胡乱糊起四周,便算完成了。最要命的是,开关在封箱的那一刻便无法关闭了,灯一旦亮起,就再也无法熄灭。
于是,这只粗陋的兔子,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,就开始了它无法回头的燃烧。它在那里,隔着布,发出一明一灭的光。那光算不得美,甚至有些刺眼,闪烁得毫无节奏,像一种急促而焦虑的喘息。
我起初是烦闷的。这无休止的光,像一种无声的谴责,照亮了我制作时的所有敷衍与马虎。它仿佛在固执地追问:既然终将废弃,为何赋予我生命?既然无心珍视,为何又给我这无法中止的光?
然而,夜深时,我凝望着它,那固执的闪烁,竟让我看出一些别的东西来。我们通常的生命,其价值仿佛系于一个开关——能自主地亮起,也能从容地熄灭,在这掌控之中,我们规划着光明的用途,计算着能量的消耗。我们相信,是这自主的“存在”与“非存在”的交替,定义了生命的尊严。
可这只兔子,它被剥夺了“熄灭”的权利。它的存在,成了一种无法撤销的状态,一种宿命般的在场。它从被点亮的那一刻起,就走上了一条单行道,只能向前,无法回头。它的全部生命,就是这“正在发光”本身。这不正是一种更为残酷,却也更为纯粹的存在形式么?
它让我想起海德格尔所说的“被抛入设计”。我们何尝不似这盏灯,被莫名地“抛”入此生,许多根本性的境遇(譬如这“向死而在”的无法关闭),并非我们所能选择。我们与它的不同,或许仅仅在于,我们拥有一个“似乎”能由自己掌控的开关,于是便生出种种能主宰命运的幻觉。而它,则赤裸裸地展现着存在的本质:一种无法退出的、持续性的展开。
它的短命,也因此有了一种悲剧性的壮烈。我们的生命,因可以“关闭”而显得漫长,可以在光明与黑暗的间歇中苟且、拖延。而它,它的全部时间,都被这不间断的光所充满、所定义。它的“一生”,就是一次完整的、持续的燃烧。从物理时间上看,它或许短暂;但从其生命内涵来看,它却以最大的密度,活完了它的全部——它从未浪费过一瞬,去处于“不发光”的状态。
那么,最终的“废弃”,意义也因此不同了。对于我们,废弃是生命的终结,是意义的彻底湮灭。但对于它,那或许只是这持续发光状态的一个必然终点,是这曲从伊始就奏响的、只有一个强音的乐章,最终在物理上无法继续而不得不停下的休止符。它的毁灭,并非对它生命的否定,反而是它这种奇特生命形式完成的最后一步。
它并非因无用了才被废弃,而是它以其全部的存在——包括这无法关闭的光,以及这光必然导致的短暂寿命——共同奔赴那个已知的废弃。它的生命与它的死亡,被那无法关闭的开关,紧紧地、宿命地捆绑在了一起。
今夜的宿舍,没有开灯,只有这只粗糙的兔子,在角落里一明,一灭。那闪烁的光,投在墙壁上,像一个笨拙而执拗的签名。我不再觉得它是个失败的作品,反倒觉得它是我所有精心构思中,唯一触及了真相的那一个。
我看着它,就像看着一个被剥去了所有自欺外衣的、赤裸的自身。它的光,并不照亮房间,它只照亮它自身那无法中止的、奔赴废弃的进程。而我们,与它唯一的不同,或许仅仅在于,我们尚且能够,暂时地,扭过头去,假装看不见那条同样的单行道。
(吴钊同:清华大学未央书院2025届学生,高中期间曾多次获得“语文报杯”中学生主题征文全国金奖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