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![]()
纪实作家的思想修养
纪实作家一定需要思想吗?以形象思维来认识与反映世界人生的文艺家,难道还要指望“思想”或“逻辑”,来掌握和表现世界人生么?
许多文艺家,看不出有什么思想,如安徒生、格林兄弟等,但依然给人以人生的启发,给人以审美的享受;而一些所谓有思想的文艺家,如托尔斯泰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,常常在作品中絮絮叨叨、啰里啰嗦,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中国古代小说,往往到最后,来一段伦理说教或道德训诫,也是很烦人的。
那么,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,并找到正确的路径呢?
一、纪实作家要有思想
作家及艺术家确实不一定要成为思想家,但无论如何要有头脑。其实,完全没有“思想”的作家及艺术家,是不存在的。差别只在于:有多少是自己的“思想”,有多少是有灼见的“思想”?
曾以柔美纯情著称的女作家茹志鹃对此深有体会。她非常感慨地说:“(十年动乱)以前,我带着一种比较真诚的、天真的、纯洁而简单的眼光来看世界,所以我看一切都很美好,都应该歌颂。……(十年动乱)以后,我的脑子比较复杂了,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也复杂了,看问题不那么简单化了,年纪也大了几岁了,的确像萧苔所讲的,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向每个人都张开美丽的翅膀。那怎么办呢?还是闭起眼睛来‘歌德’?我过去的作品里的确极少写被批判的人物或反面人物,这种人物我几乎没有写过,所以有人觉得我不善于写尖锐的矛盾。现在呢?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物,我看见了,而且看见他们正是横在我们向四化进军的道路上。我不能闭起眼睛,更不能避开生活,要写这样的人,要鞭挞不正的思想作风。这些对我讲起来都是一个新的课题,通过为数不多的几篇作品我在进行试验。”显然,思想的深化,使茹志鹃新时期以来的作品,得到了明显的深化和提高。于是,她强调:“我们要思想,要思考问题,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,发生在我们政治生活当中的具体事物进行思考。这一点,不管我们是不是思想家,只要你是搞创作的,一定要做。”(《作家谈创作》上册,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,第667、661页。)
从世界文坛发展趋势看,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,文艺与哲学思想日益走向密切结合。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间是如此,存在主义哲学与艺术更是如此。
对于存在主义要多说几句。以小说《审判》《变形记》和《城堡》闻名的奥地利作家弗朗茨·卡夫卡(Franz Kafka),在其作品中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、孤独和无助,成为存在主义文学先驱。而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让-保罗•萨特,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在他的文学作品如《恶心》、戏剧《禁闭》《苍蝇》中,深刻探讨了人的自由、存在和虚无等哲学问题。另一位存在主义和荒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尔贝·加缪(Albert Camus),在他的作品《局外人》《鼠疫》和《西西弗斯神话》中,则探讨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和意义。这些作品对西方后现代社会及其中的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随着我国融入世界大家庭,存在主义大师们以文学+哲学方式所揭示的问题,很显然已在我国各个层面显露出来。存在主义所提出的思想,尽管有偏执,有错讹,但许多方面并没有过时。我们需认真对待。
但不能以为:有了深刻思想,必然就有艺术上的成功。这一点,我们往后再讨论。
当然先知先觉者,会为我们提供前行的方向。莎士比亚很早就认识到金钱的缺陷与资本的弊端;巴尔扎克更是深刻揭露了支撑资本主义大厦各个方面的罪恶;萨特等对人类存在及其意义的忧虑,依然是人类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。

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与创作,依然警示我们
二、纪实作家要有独到的见地
人的见地,包括有思想,还有观念,乃至智慧。智慧乃是思想的最高境界。
具有独到见地的作家,不会盲从,人云亦云。即使在古代中国,屈原、司马迁、陶渊明、韩愈、杜牧、苏轼、文天祥、李贽、曹雪芹等,都因有主见脱颖而出。在当代,也有一位杜鹏程,人们都记得他的《保卫延安》。其实他于1957年7月发表的《在和平的日子里》,在当时就有两条重大突破:一是进城后有些共产党老干部意志衰退,一是优秀知识分子是建设的重要力量。这都是与他长期坚持独立思考的结果。然而,请记住这个时间节点,许多人都不理解,甚至予以非难。但杜鹏程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如今时过半个多世纪,其中对官僚主义的针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,依然给人以启迪。
即使是曾经正确的思想,也可能僵化成为教条。“文以载道”本不错,但儒家学说中,许多“道”逐渐成了思想的束缚。忠、孝、节、义等,曾经都是有一定合理性的,但大多数则与现代性背道而驰;还有等级观念、女性歧视、奴性态度等,也在中国历代文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。因此,要对此保持适当的警惕。我们不能苛求前贤,但我们自己不能有“遗毒”。
人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。所以再伟大的人物,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有时代缺憾与历史局限。
就文学领域来说,常常会出现两种情况:
一是作家随时代进步而进步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鲁迅。瞿秋白在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中指出:鲁迅“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,从绅士阶级的贰臣逆子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,以至于战士。”这是对鲁迅思想发展演进的至论。
随时代进步而进步,其实也有一定的“危险”。二、三十年代成名的现代中国作家,大多“思想进步、艺术退步”,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。鲁迅先生反正是去世了,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曹禺、赵树理等,五十年代后所写的,均逊于他们此前的作品(唯有老舍先生例外)。
而最典型的是丁玲。她的“起点”是比较高的,30年代就有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;40年代后,陆续有《在医院中》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等。她本来就激进,获得“斯大林文学奖”一等奖之后,更以为“一本书”能如何。好像在进步,却是在游移、偏离。她被打成右派,实在是“历史的误会”;果然,“归来后”(右派作家的文集),人家都反思、反省;她可好,比勇于自省、敢于“请罪”的周扬等还不如,令人唏嘘。
一是作家僵化,固步自封,反而落后于时代,由进步转为落后。最典型的如果戈里,居然去讨好、献媚沙皇,为当时的俄罗斯几乎全体文人所不齿。我国的“西望”先驱之一林纾,也与之接近。
戊戌维新前,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。所作《闽中新乐府》50首,体现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。之后林纾思想转向保守。到辛亥革命后,更趋“反动”,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“庸妄巨子,剽袭汉人余唾”。五四运动中,《新青年》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。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,坚决反对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。他还发表了两篇小说:一是《荆生》,一是《妖梦》,影射攻击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等人,终于被历史巨浪淹没。
每位具体的作家,无疑总是有思想局限性的。托尔斯泰有,高尔基同样有。所以列宁才不厌其烦地给他写信,连批评带鼓励地帮助他。当然,他们都有所克服。所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,是高估了创作方法的作用。其实是现实的教训,以及他们世界观本身的矛盾,使他们不同程度上获得了真知。
要获得独到见地,超越时代局限,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。菲利普•巴格比谈到一个天文学发展历史突破的一个例证:“开普勒连续做了十八次努力,企图证明行星以圆形轨道环绕太阳旋转。他相信柏拉图的权威,认为圆形是运动的最完美形式,所以上帝在创造太阳系时,必然为行星安排了这种最合用的轨道。事实上,上帝并没有受人类这种对圆形的偏爱的引导,只有抛弃这个基本假设,开普勒才有可能发现行星是以椭圆形轨道运行的。”(菲利普•巴格比:《文化:历史的投影》。夏克等译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,第3页。)虽然是自然科学研究,但却让我醍醐灌顶、茅塞顿开,对于文艺创作与研究也是很有启发性的。当今我们不断强调全局思维、前瞻思维、底线思维以及发散性思维等等,就是要打破陈规旧习,获得创造性思维,而文艺创作正是最需要发挥创造性思维的领域之一。
对独立思考,也不能过于自负。在真理面前,固执己见就显得顽固不化了。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个性和思想的理论家,他提出的“到处有生活”“主观战斗精神”“精神奴役创伤”等都很有创见,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一定的正确性。但置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,就未免有偏颇。因此,才引致邵荃麟、何其芳、黄药眠乃至胡绳、乔冠华等一众作家评论家的批评。如果胡风不自负于自己的独立思考,而适当听取当时还属文友的意见,或许就不会酿成后来的历史悲剧了。

外交家乔冠华偶尔涉及文艺评论,也很有高度
三、纪实作家要有正确的观念
独到不等于正确。一切观念都应从实践中来,并经过实践不断检验。当然,关于“实践标准”,其实也要深究。什么人(个人与群体)的实践,哪些方面的实践,何时何地的实践,等等,都有讲究。还有,有些问题,永远不是人的实践可以证明的。对此,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。由此亦知我们人类的根本局限所在。
对于作家来说,我们的思想、观念还是要坚持实践观。以社会实践来检验,人类的思想就有先进与落后(从前还常说“革命与反动”,到了如今我们也按下不表罢)、新颖与陈腐、深邃与浅薄、丰富与单调等的区别。
别的也不在这里展开了,因为大家已经说得太多,有些说法或许还会让作家们感觉不适;这里就特别说一下“丰富与单调”,因为人们很少讨论这个问题,却每天要予以面对。
现代信息社会,人人都通过网络、手机、电视等接受大量信息。经常被“带节奏”,却很少去厘清,或者也没办法去弄清。于是人云亦云、随波逐流。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思想、观念,而无所适从。普通人如此,只能指望他们从中慢慢吸取教训吧。作家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社会成员,却不能如此。但也不宜走另一个极端,死抱着几条观念,而是要像列宁说的那样:尽可能地“吸收人类的全部思想财富”。
就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,也要有正确的态度。著名外交家乔冠华,一度也涉猎过文艺评论。在署名为“乔木”的《文艺创作与主观》一文中,他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:“马列主义的思想只能帮助我们观察、分析和研究一切具体的对象,它不能代替这种观察、分析和研究的实际工作。而作家这种正确分析和概括的能力,却是从这种长期观察、分析、研究和判断的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的。”他具体阐说道:“马列主义的思想只能一般地教育我们爱和恨的主要方向,但它却不能代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爱这个应该爱的具体人物,或者恨那个应该恨的具体人物的真爱和真恨的实际生活。”(乔木:《文艺创作与主观》。载《大众文艺丛刊》1948年第二辑。)可谓鞭辟入里。然而,几十年过去了,还是有一些作家及文学管理者对此执迷不悟。
扩而言之,对人类所有的思想,都应当持辩证态度。
任何高深的思想、崇高的理想,尽量要能接地气,与实际生活、与群众感受息息相关。如此才能走入人们心中,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。白桦对此有过刻骨铭心的体会:“不可想象,如果你的思想性十分正确,让人挑不出毛病,而且非常美妙,可就是和生活不对号,和群众不对号,那么你的思想性,那个正确完全是假的,不是生硬的说教,就是反动宣传。有些作品我们的确从理论上思想性上挑不出毛病,哪一点都可以在经典著作中找出来,结果观众就是不要看。观众说,这和我毫无关系,和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(白桦:《历史的回顾与思考》,《戏剧艺术》1978年第1期。)白桦说得有点激愤,与生活和群众“不对号”,倒也不至于就会成“反动宣传”,但他的基本意思大家都明白。因此,作家务必要有这样的群众意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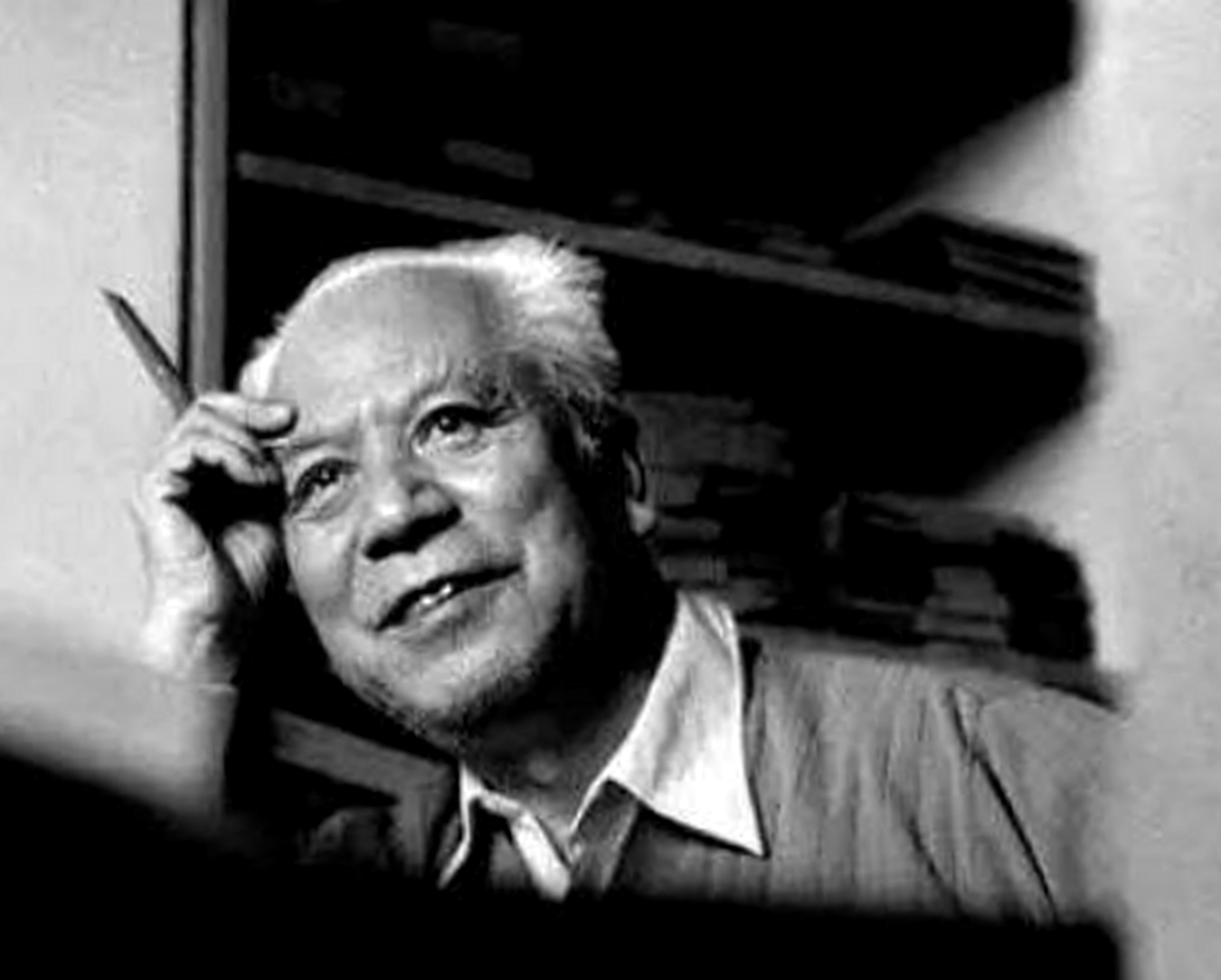
可敬却可怜的姚雪垠,枉费心机在李自成
四、将思想与情感交融为生动形象
思想的高度不等于艺术的高度,思想的精辟不等于艺术的精彩。
作家艺术家还要把得自别人的思想,或自己感悟到的思想,凝聚于艺术形象之中。因此,要把思想与取自客观的映像结合,与作家的情感密切融合。——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本来是统一的,但许多作家却割裂了,因此造成了形象的分裂。
姚雪垠对李自成那个热爱啊,恨不得把他塑造成“杰出的共产党领袖”,让吴晗都看不过去。但小说又不能不受历史上真实的李自成制约,于是,李自成的形象是高大了,却让读者觉得不太可信。此前,浩然写高大泉;后来,二月河写康雍乾,虽然对象面目悬殊,但底色却一样。
另一方面,巴尔扎克恨死“高老头”之类,却写成让人深感同情;早先,罗贯中厌恶曹孟德,但写着写着,还是让人觉得这曹丞相确实是个人物。
所以,现今的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,还是先要“思”清楚、“想”明白。
同时,即使是再先进、正确、新颖的思想,如果不渗透于形象之中,对于创作来说,依然是失败的。其实,对于“思想”本身,也是有损害的。
两位博学的美国文学教授雷•韦勒克和奥•沃伦,在其合著的《文学理论》中,单列“文学和思想”一章,考察二者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。他们提出疑问道:“难道因为它们(指哲理性的小说与诗歌)输入了哲学内容就可以算是卓越的艺术品吗?难道我们不要做出结论说这样的‘哲学真理’正如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真理一样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吗?哲学或者思想意识的内容,在恰当的上下文里似乎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,因为它进一步证实了几种重要的艺术价值:即作品的复杂性与连贯性。一种思想认识的见解可以增加艺术家理解认识的深度和范围,但未必一定是如此。假若艺术家采纳的思想太多,因而没有被吸收的话,那就会成为他的羁绊。”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证太多了!如何有效地让思想与形象融合呢?他们精辟地提出:“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,成为其组织的‘基本要素’,……思想放出了光彩,人物和场景不仅代表了思想,而且真正体现了思想在这种情形下,哲学与艺术确实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致性,形象变成了概念,概念变成了形象。”(雷•韦勒克和奥•沃伦:《文学理论》,刘象愚等译。三联书店1984年版,第129、128—129页。)
这与恩格斯“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36卷,第386页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。)的要求异曲同工之。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对文艺创作中的“倾向”问题作过多次深刻的论述,并不约而同地对席勒把文学创作当做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”的做法予以批评,因为“席勒式”不仅失却了艺术的力量,也冲淡了思想的力量。可惜这样的错谬,后来却反复“上演”。纪实作家应当吸取教训,让思想的光辉经由鲜活的艺术形象闪耀出来。
(待 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