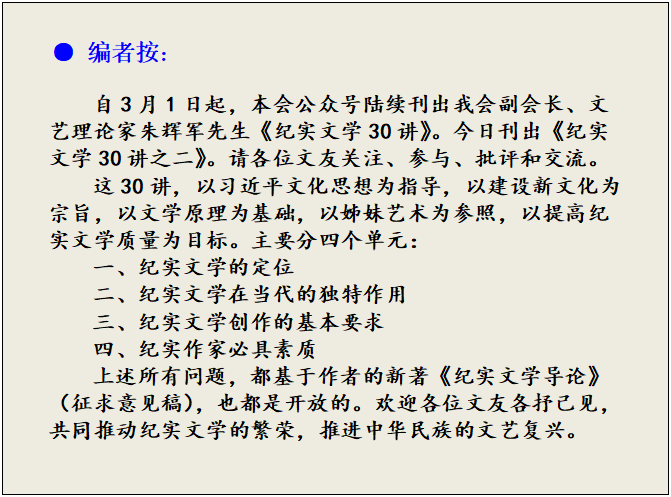

![]()
再现与表现
再现与表现是文艺创作的两种主要方式,也是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。这两个重要概念,与写实和写意密切相关,并且是现实主义、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、象征主义、表现主义等的基础。
1、再现源自人类掌握外在世界的内驱力
再现,即对客观事物予以真实的呈现。这个问题因此与纪实文学尤其有十分紧密的关系。
为什么要逼真地再现对象呢?我们要从人类渴望认知和掌握客观世界的深层原由上来理解。人类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从来就充满好奇。与大多数动物只停留在好奇不同,人类还想掌控和利用客观外物,所以先要了解它们。同时,我们中国人看到的,西方人不一定看得到,反之亦然。尽管如今已进入“地球村”,但还是有许多人们难以企及之地。更重要的是,东西方看到的世界,受文化传统等的影响,可能还很不相同。这有点类似人类与猫头鹰视野的差异。所以,再现客观世界,而且越逼真越好,乃是人类求知、生存、发展的必要。
柏拉图不懂这一点,因此误认为再现(他与古希腊哲学家一样,用的是“摹仿”)不过是“复制”客观对象的影子。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摹仿的是“动作”,将对象的运动状态纳入再现之中。以后,人们认识到,对于人物的再现,要努力呈现出“性格”。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,则提出了“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》<一>,陆梅林辑注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188页。)这是“再现论”逻辑发展的结果,也是这一理论迄今为止的最高阶段。
再现“动作”和“性格”,许多艺术样式都能完成,甚至雕塑也能做到,如《拉奥孔》。《拉奥孔》的艺术处理,对后世绘画、摄影等影响深远。而再现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,绘画、雕塑、摄影等就不免十分吃力,文学、戏剧、影视等于是在此大显身手。
其实,就是再现对象的静态,也依然为人们所欢迎。中外都有许多逼真的风景画和人物画,西方甚至单设一门“静物画”。在这里,人们更多地赞赏艺术家精湛的技艺。
古今中外这样的例证不少。还在三国时,东吴著名画家曹不兴,有一次入宫为孙权画屏风。画到一筐杨梅时,不小心误落一点笔墨在画屏上。旁人都替他捏把汗,而他并不惊慌,随手将墨点绘成一只振翅欲飞的苍蝇。孙权来看时,以为真的苍蝇飞到了画上,举手要把苍蝇赶走。这就是“误笔成蝇”的来由。就算孙权眼花或近视,曹不兴的功力也依然属是异乎寻常。无独有偶,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乔托,有一次在一幅肖像画上画了一只苍蝇,画得是那么逼真,以致连他的老师、同样是著名画家的西麻布,居然拿起刷子要把它赶跑。
中国的曹不兴与意大利的乔托之间,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们有交集,却有着不约而同的记载!其中或许有夸大的成分,但也说明画家的扎实功力,和人们对逼真描绘的普遍痴迷和推崇。
2、逼真再现,需要扎实功底
能够把对象再现得栩栩如生,真的是需要非常精细的观察和深厚的功底的。
当然,这里基本不涉及艺术性的高低。人们主要用真实性的标准来要求,所以几乎人人都可以依据原物来提出意见。唐代著名画家戴嵩,以画牛著称。但他的传世之作《斗牛图》,却让牧牛童找出了破绽。原来,戴嵩画的斗牛,虽然剑拔弩张,可牛尾却高高的竖着。这是违背事实的。牧牛童多次见过,牛在争斗时,牛尾是使劲夹紧在两腿之间的。可见,真实准确地再现客观事物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
甚至可以进一步说,大部分以假乱真的画作,其艺术性并不一定高。把罗中立的《父亲》与冷军的《肖像之相——小姜》作一比较,高下立显。这里最大的不同,就是“神似”与“形似”的区别。此外,罗中立的画作中还负载着深厚的历史内涵,这是许多写实画家所不具备的。
尽管西方人没有说到“神似”,但他们在实践中却也有类似的追求。“神似”,首先要求再现对象的“神采”,更进一步,则要再现出对象的“神韵”。这里我们先不表中国的例证,仅说达•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,就足以证明西方的艺术大师是深知其中三昧的。
这一点对纪实文学创作格外重要。不少纪实作品往往停留于机械地“复制”对象的外在行为,显得毫无生气和韵味。所以,要努力再现出对象的神采和神韵,这样才能避免落入窠臼。

亚里士多德,再现理论大师
3、艺术再现的特殊价值
再现存在的价值,除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外,还有一个重要方面,就是认识历史、了解历史、留住历史。
按说,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。但人们从不满足历史学家的记载,而是诉诸文艺家的形象描绘。甚至像左丘明、司马迁、希罗多德等也借鉴文艺家的方式,以求生动形象地记载历史。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:“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,一用散文,一用‘韵文’;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‘韵文’,但仍是一种历史,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;两者的差别在于,一叙述已发生的事,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。因此,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,更被严肃地对待。”(亚里士多德:《诗学》,罗念生译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28—29页。)诗人(以及大多数文艺家)的创作,在他看来,比史书更真实。
在中国,历史文学、历史剧、历史人物画等更是空前发达。这些作品不仅仅只是历史的补充和拓展,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历史,并满足了人们对历史的怀念和想象。
对历史的想象,自然不完全是再现的,往往还杂有传说、演义。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荡寇志》等莫不如是。但其主调却是再现的,甚至连那些传说、演义等,人们也宁肯认为是真实发生的。
对同一现实或历史的再现,往往会出现很大差异。
因为这种差异,使文艺理论家们对再现本身也进行了考察和反思。事实证明,并不存在与客观完全一致的再现。H·G·布洛克在《Philosophy of Art》(中译本为《美学新解》)通过大量事例充分说明了:再现并不是对现实的复制。他指出:“我们已经提出四个主要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艺术再现不同于客观现实。这四个理由分别是:艺术家的个性、某个时代的文化观、某个时期的艺术风格、使用的艺术材料。其中每个理由都能在现实和再现之间作出区分,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,艺术品并不是现实的抄录,而是对现实的解释和再现。”(H·G·布洛克:《美学新解》,辽宁人民出版社,1987年版,第63—64页。)H·G·布洛克的分析鞭辟入里、令人信服。
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,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,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日益深入,对艺术上再现方式的探索也日益丰富。为什么摄影、摄像技术已高度发达后,人类还重视文字、音响、图像、身姿等的再现呢?
各种艺术的再现方式原则一致,但形态大不一样。文字的再现,是最玄妙的。一般说来,文字本身并不具备再现功能。即使是象形文字,也只是模拟了对象,绝不能做到像绘画、摄影那样逼真地呈现对象的形态。那么,以文字再现客观世界,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?
我们不妨看一段再现文字,再比较这段文字与图像的差别:
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;看起来厚而不腻,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?我们初上船的时候,天色还未断黑,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恬静,委婉,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,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。等到灯火明时,阴阴的变为沉沉了:黯淡的水光,像梦一般;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,就是梦的眼睛了。
对于秦淮河,不知有过多少钟情的画家、摄影家留下了他们的作品。然而,就是将作品“看穿”了,也找不到朱自清在《桨声灯影秦淮河》的感觉和韵味。文字的妙处是图像永远不能替代的。
4、表现并不限于主观感情
一般认为:再现指向客观世界,而表现传达主观感情。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认为,表现主观感情,比再现客观世界更重要。
表现情感,哪是否与纪实文学关系不大呢?
我们论述过“纪实”中的“实”,是现实的,也是历史的。这是从时间轴来看的。那么,从“实”的类型来看,有“实事”及实景、实物等;还有一个重要方面,就是“实情”。“实情”可否“纪”呢?
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。而从创作实践看,也有不少例证。丁玲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可以说十分典型。这部日记体小说,带有很浓郁的纪实风格。丁玲所“纪”的,有她自己的心绪,也有她两个好友杨没累和吴绍芳的感受,所以才引起广泛共鸣。那么,丁玲对三位知识女性情感的披露,算再现还是表现呢?显然是兼而有之的。
被表现的情感,其性质、状态也都大有讲究。情感有大小、有高低,还有厚薄。所以,对那些狭隘的“自我表现”要保持警惕。
除了情感之外,还有别的吗?中国古人其实更注重“情志”。刘勰所言:“人禀七情,应物斯感;感物吟志,莫非自然。”(刘勰:《文心雕龙》,中华书局,1980年版,第57页。)是最为精辟的论断。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。
进一步说,艺术表现出的情感,并不一定是艺术主体当时体验的情感。虽然许多时候是如此,如郭沫若写《女神》时,就是这种喷涌而出的状态。但时常也有不是这种情况。如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中,维特因失恋而痛不欲生,这确实也是歌德曾经体验过的;但在“表现”这一段时,歌德自身的情绪状态已经平和了许多。因此,不能把维特的情感状态,等同于歌德创作时的情感状态。优秀的作家艺术家,往往是在反复体验、咀嚼甚至思考自己的情感后,再“表现”出来,因而更能久久打动人心。

克罗齐,表现理论大师
5、再现与表现的互补和共存
不能把再现与表现看成是完全对立的,二者其实是互补互益的。
在许多作家、艺术家那里,往往交替使用再现与表现的方式,获得了最佳效果。上述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都属于这种情形。
对于客观的事物,除了再现外,是否可以“表现”呢?
从中国人的创作实践看,显然是可以的。因为在中国人看来,万物皆有灵。世界的“灵性”与人的情感相通,因此当然可以“表现”。而且中国古代文人十分擅长这个。这与“写意”方式有一定关联。但对客观世界的“表现”,又不仅仅限于写意。而是要努力体现出宇宙万物的律动来。
中国的画家往往就用“再现”的方式,去“表现”出世界的韵味。这是非常高妙的艺术处理。他们追求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,此处的“言”,当然不只是指“语言”及文字,而是涵盖了整个艺术形式。而“意”,则不仅指有形因而有限的物像,而是经由这物像指向更无穷的宇宙。最典型的,就是中国文人对“梅兰竹菊”等的描绘。
往深里说,极少有纯粹的再现,或纯粹的表现。所有的再现,都必须经过作家或艺术家的脑与心,所以对客观事物的“再现”,必然是通过文艺家的心灵“表现”出来的。对于秦淮河,朱自清和俞平伯都“再现”过,但二者有同异。同的是描绘同一对象,而因两人志趣的差异,同样的秦淮河呈现出了不同样貌。而对内心情感的“表现”,往往也要通过对一定对象的“再现”来加以体现。比如抒发爱国情感,就需要有长江长城、黄山黄河、国旗国徽等作为载体。否则,像十年特殊时期那样反复吼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很好,就是好,就是好……”,吼一千遍也无效。由此可见,再现与表现是相互依存的。
从更高层次来看待再现与表现的互补,就是对世界人生内外的完整展现。这个世界,不只是外在的景物和人类的活动,这个世界“有情”,就是因为生活着许许多多拥有丰富情感的人们。文艺因此不能只注重外在,同时也要深入人类的心灵。再现与表现这两种主要方式,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实现了高度的互补。
( 待 续 )
![]()